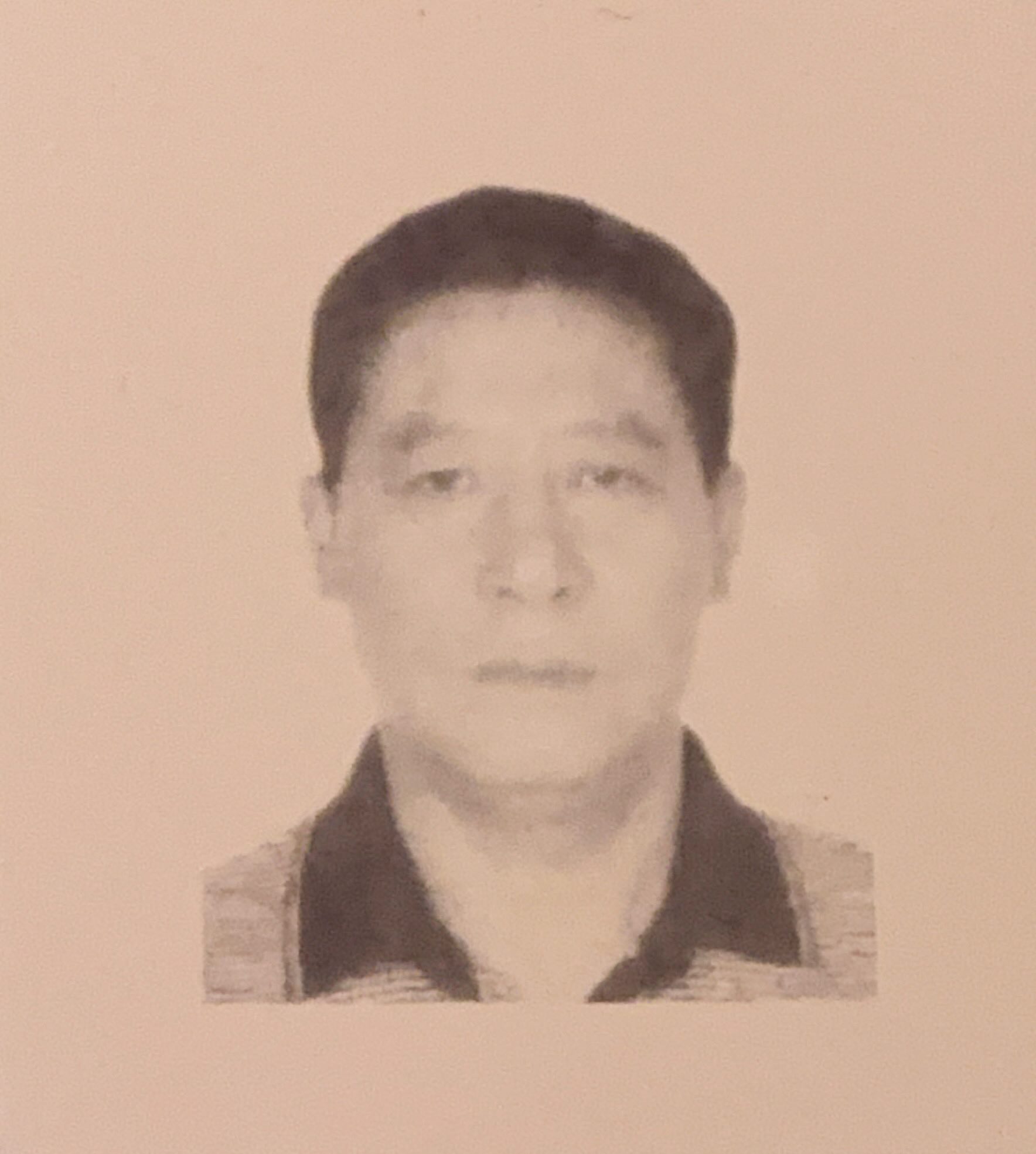我的父亲
儿 玥 2024/12/24 6:28:00 浏览:326
我的父亲1952年12月18日生,属龙,2024年12月22日去世,享年72岁。
我对父亲的记忆,大约从两岁开始。那时,我们一家和爷爷奶奶、老叔一起住在河北区小王庄街道。爷爷奶奶共有四个孩子:大姑、我爸、老姑、老叔。从我有记忆起,大姑和老姑已经出嫁住在外面。我们一大家人住在靠近铁道边的一处半违章建筑里(有几间加建房子没报批)。靠马路的一端是爷爷开的简易小饭馆,面向普通工薪阶层,主打面食和炒菜;后面几间房则是卧室。那时家里还有个小院子,养鸡养猫,整日嘈杂。
父亲是“老三届”。他初中没读完就去上山下乡,在河北的一个郊区务农(他常笑我小时候胖,说他16岁下乡时只有85斤,而我小学三年级就超了他)。恢复高考后,他凭借平时的大量阅读和写文章的天赋,考上了师范大学中文系,这在当时非常难得。父亲在大学准备毕业论文时,我也出生了。小时候,我对他的印象比较模糊,更多是和母亲,爷爷奶奶,老叔相处,以及听见旁边铁道上时常鸣笛的火车。父亲是家里的长子,因为爷爷奶奶关系不睦,他常在两人间奔波调和。我小时候以为他比较偏向奶奶,可后来才知道,他对爷爷也怀有深重的感情。
父亲毕业工作分配到了司法局,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和爸爸妈妈一起搬到了师范大学里面的家属楼,而我就自己走路去大院里面的幼儿园。我们三个人只有一间不算大的房间,厨房厕所是和同一楼层的几家共用的。这段时间的记忆也有些模糊了,就记得晚上爸妈会拉上我出去门口的吴家窑大街散步,那时候八里台立交桥还在修,晚上可以在空荡的工地上跑来跑去,父亲会逗我跑圈追他捉迷藏什么的,从小帮我打下了一些运动基础。很少的时候爸爸还会带我们去当时极少见的西餐厅里去潇洒一把,点杯咖啡一家人喝,苦的我觉得以后都绝对不会碰这个东西(当然后来是完全相反的)。当时家里已经有了一台手动机械照相机,但是胶卷还是很精贵的物品,所以我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些少量的和爸爸妈妈的家庭照片留存下来。
在师范大学的时间大约只有一两年,我也上小学了。我们分到了新的房子,在隔着吴家窑大街对面临着废墙子河(当时就叫“臭河”,因为真的很臭)的一个6层楼房里。这一次,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厨房厕所,也有两个一大一小的房间(俗称“偏单”)。在这里我开始上小学,中午就走路到父亲的单位吃饭。父亲在单位里总是很忙碌的,基本上给我准备好饭就去忙别的。吃饭的时候我大部分时间是自己看办公室里的报纸,一般都是机关里面很正统的刊物,但我也能读下去,现在想想是从小培养了我喜爱阅读的习惯。吃完午饭我就和大院里的其他小朋友打乒乓球做游戏什么的,那段时间是我一直很怀念的童年时光。虽然不太懂父亲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偶尔看到他在办公室里写东西,和同事聊天,有时还听同事说他有很重要的报告什么的,忙的时候爸爸在家面也会连夜写文章。爸爸的字写得很好也很快,很少有错字,而且字体就是自创的没有什么流派。
我上中学时,父亲开始做律师,组建了天津市第三律师事务所,当时是从政府剥离、自负盈亏的改革先锋。他的办公楼就在我学校附近,但我很少去,因为学校包中饭。不过有需要时,找他倒也很方便。父亲做律师后,情绪明显高涨,我想是因为他能掌控和影响更多事,而且收入也随努力增加,动力自然不同。不过工作压力更大,他本来就是急脾气,又经常昼夜不分,所以对家庭和睦也带来一些影响。各种应酬多起来,晚上常不回家吃饭,喝醉有时还会耍“酒疯”。我和母亲都挺反感,虽然理解是工作需要,但也难免产生家庭矛盾。最糟糕的是,他的身体健康开始恶化,高血压和糖尿病接踵而至。可由于症状还不明显,他不大在意,也不按时服药。这些都给后来的健康状况埋下了隐患。
我去上海上大学后,回家的次数骤减,寒暑假各回一周左右。平时每一两周给家里写封信汇报近况,我倒是一直坚持的;父亲有时会回信,还是我熟悉的流畅笔迹;偶尔也父母打电话到宿舍,但一般主要还是我妈说话多。大学后,我对家里了解越来越少,只知道父亲的高血压、糖尿病没有起色,但也没法想出更好的办法来督促他。
等我去美国读研究生,回国的次数就按年来算了,而且每次只停留几天,跟亲戚朋友聚一下,很少真正能和父母坐下来聊天。读书期间,我邀请父母第一次来美国,可当时住的一居室条件简陋,而且学校所在的地方在美国的偏僻乡下,没车就哪儿也去不了。父亲就自己找事做,比如去附近小超市搜寻打折品转手卖,或在跳蚤市场淘点“文物”带回国之类,总之闲不下来,但也沉不进去。
我和太太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由于需要人照看小孩,我和父母相处的时间一下子增多。那时我和太太在硅谷的激烈竞争氛围里,工作与带娃都很辛苦,尤其第一个孩子又没什么经验,就两边的父母轮流来帮忙。轮到我父母时,主要是母亲做家务,父亲就负责带孩子出去玩。那时父亲的律师工作已逐渐清闲,一来是大环境如此,二来身体也不好,母亲希望他少干活,多关注健康。在美国时,他就像放了个长假,我也能“盯”着他少抽烟(很多美国地方室内禁烟),按时吃药,多锻炼,带他们四处旅游。我们三代人一起走了不少地方,留下许多照片和回忆。但一回到国内,父亲又重拾不良习惯,而且在家没什么工作,就干脆通宵在电脑上玩单机纸牌。母亲管不住,只能随他去。我每次电话、视频也是老生常谈,收效甚微。
2015年夏天,我把三岁多的老二放在国内父母家,一方面爷爷奶奶能多陪孙女,另一方面也让我和太太喘口气。一天晚上,我和太太刚看完电影出来,接到我妈电话,说我爸中风进医院了,情况不算明朗,让我别紧张但尽快回来。我立即买了最快的机票,18个小时后就赶到家门口。亲戚们在等我,然后带我去医院。父亲在ICU里,我只能隔着玻璃窗远远看见他昏睡,头上戴着医用头套,做过手术的痕迹清晰可见。第二天早晨,我终于被允许进入探视时,他还在昏迷中,身上、鼻孔和嘴里插满各种管子。我默默祈祷他一定要挺过去。后来医生说他有了意识,可以简单表达,但因为肺部感染,出院康复要推迟,这也会影响总体康复效果。我当时对中风知之甚少,对病后康复却抱着相当大的希望。大约一周后,医生终于说可以去康复中心开始复健,但父亲依旧极度虚弱,需一直挂着盐水。医院介绍给我们一位护工小王,他也就成了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陪伴在我父亲身边的人。
接下来的康复过程反反复复,非常艰难。父亲左半边身体几乎没有知觉,需要一步步重建神经触动,重新学习并适应新的行走方式。可他对锻炼本就排斥,个性又倔,小王性子也直、要求严格,常常矛盾不断。我和母亲期待父亲至少能恢复比较完整的自理能力,但如果不能坚持练习,效果当然有限。父亲一度可以靠拐杖缓慢走路,却最终没能保持下来,身体状态又回到需要随时有人帮助的地步。父亲和小王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最终我和母亲只好把他送到养老院。我那一年里在中美之间往返20多次,经历了无数次希望与失望的交替。自从父亲进养老院,母亲开始了每天白天去看他,晚上回家休息的模式;我回国的频率也降低到大概半年一次。
2019年底,我刚回国探望过父亲,新冠疫情就席卷全球,导致中美交通几乎中断。养老院也实行封闭,母亲长期无法探视,只能靠电话询问或等待护工消息,这也让父亲的康复监督进一步削弱。一直到2022年,世界各国顶不住压力开始逐渐放开,中国的隔离政策也有所松动。我在10月份向公司请了三周假,一半用来落地隔离,一半再去看望父母。隔离政策那时还是很严苛,健康码几次莫名出问题,波折不断才拿到养老院的探视许可。那也是母亲许久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三年未见,我看到他见到我们的时候眼中好像闪过一丝光芒,但因长期缺乏锻炼,他的身体机能下降得更厉害,已经完全无法自己完成站立的动作。新冠对无数家庭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我们也是受害者之一。2022年底,全国防疫彻底转向全面开放,不到一个月很多人染疫又自愈,母亲也不例外,但还好父亲在相对封闭状态下没有染病。2023年暑假,我带孩子们几年后再见到爷爷,他眼里再次闪现光芒。但孩子们依旧难以理解他经历过什么,就像当年我只知道父亲让我去看爷爷,却并不知道该和爷爷说些什么。2024年暑假,我再带妻女回国时正好赶上父亲节,生平第一次给父亲买了束鲜花,还请大家庭聚餐合影,没想到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虽然我和父亲从来不是十分亲密的关系,但我从他身上还是学习了很多东西。父亲给我最大的启示是,许多事情不一定要循规蹈矩,另辟蹊径也许会有更好的结果。他一直喜欢与众不同,这在他的时代相对少见。也正因如此,我对美国文化里“take risk”这一理念适应得很好,在硅谷的科技浪潮中也如鱼得水。回想起来,这与父亲当律师时的经历不无关系:每一个案子都需要独特的视角才能出奇制胜,若按部就班,律师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出去旅游时,他也总爱带着我们走那些没有明显标识的崎岖小路;有时是曲径通幽,有时则要无功而返。我也渐渐习惯了这种旅行方式,多走点儿路也不在乎。
不过,律师工作对父亲而言虽然合适,却也因为行业的起伏和时而紧张、时而松懈的节奏,对他的身体造成巨大损伤。高血压常常高到可怕的程度,糖尿病也很早就找上门。由于父亲自己对吃药不上心,从未得到很好控制,再加上锻炼意识薄弱,我和母亲总担心他什么时候会出事。也确实发生过多次惊险的状况。比如我老大刚出生不久,父母来帮忙,有点时间他就忙着收集废纸盒去卖钱。有一次,他整理废物是打喷嚏突然鼻子血流不止,卫生棉球塞了也没用,我们在美国又没有医保,先是跑中医药店无果,再去一家给穷人服务的诊所,简单处理后仍复发,最后不得不在斯坦福大学医院做手术——既昂贵又吓人。好在术后把鼻腔血管烧灼封闭才控制住。我们赶紧让父亲回国静养,避免他再出意外。想必类似的经历还有多次,只是我不了解全部细节。
父亲最大的缺点,恐怕是不听劝也不自律,常常随心所欲,还有一些自认为正确、难以辩驳的理论。比如他爱吃夜宵,常是馒头加咸菜,这对糖尿病患者很不妙;又比如每天一两包烟,还经常在屋里抽,尤其冬天室内空气糟糕。吸烟让他肺部更脆弱,也为将来埋下隐患。再加上作息不规律,没事时他能整天躺着睡,起来就吃东西或窝在床上看书(后来还学会玩电脑纸牌)。有业务时又昼夜不停地干活,大量抽烟喝咖啡。对于电子邮件或上网等新科技,他认为根本用不着学,有我妈就行,还觉得看报纸更靠谱。这多少也让他与时代主流脱节,乃至心生不满。当然,这些可能是他那一辈人都或多或少常有的特点。
在父子关系上,我记忆里父亲和爷爷很少说话,偶尔说上几句也常常会变成吵架。然而,暑假里,父亲时常会叮嘱我抽空去看看卧病在床的爷爷。我就骑车顶着太阳骑一个小时自行车过去,见到爷爷喊声“您好”,坐一会儿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再去外面看书、写作业。过半天再同他打个招呼就回家。回到家,父亲就问“爷爷怎么样”,我简单说“还好”。后来爷爷在我初中时去世,父亲痛苦了很久,天天待在家,看许多佛教书籍,研究转世轮回与生命延续。看得出,他对爷爷的感情非常深。我不想和父亲走到他们那种形同陌路的境地,所以从中学开始,我尽量克制自己,不太和父亲争辩,即使有时特别不忿也会自己化解。这样一来,我整个青春期和父亲的关系也是比较融洽的。长大后,我对父亲对家的贡献和对我的培养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多了更多的敬意。但是无论如何,男人之间的交流,不论再亲密,也很少能带上太多感情用语。我和父亲的关系就是这样。
爸,儿子想念您,愿您在天堂一路走好!
- 暂无评论!
- 发表评论文章评论(共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