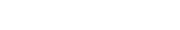怀念一个干净的人
段增勇 2020/10/24 15:01:00 浏览:263
怀念一个干净的人
昨晚,在西北的寒风里,那份清冷感觉,很是惬意,我说有“凉快”的感觉,引来西北同仁的欢笑。
夜深人静了,凌晨一点了,竟然是辗转反侧,心慌意乱得一塌糊涂,我担心了我的心脏,我变化了各种姿势,尽量让我的内心感觉了舒适,而进入睡眠依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也不知折腾成啥样儿了,大概凌晨三点过,迷迷糊糊了我的睡眠。
7点左右起床了,习惯性翻看手机,收到我的首届学生我恩师的儿子凌晨两点三十六分发来的短信,“爸爸于今晨走了,非常感谢你们一直的关心!”我的心紧缩着,马上拨通电话,无比慌乱中的言语,已经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岁月的沧桑,早已收走了我的眼泪,我也就继续慌乱了与我的恩师我的老校长的儿子电话了相关事宜,同时给各个地方的部分高中同学又电话了一通。
我想,今天的一天里,更多的同学一定相互沉痛了心情,传递这个噩耗。
今天一天里,我努力克制去做被要求做的事情。然而,我的思绪却回到了22年前,丝丝缕缕的,都是这42年时光的一些细碎,与陈老师相互关联,与我生命经行中的某些记忆关联。
此刻,又是凌晨了,不是心慌意乱而睡不着。这个“半山亦景”的酒店里,听外面是稀稀落落的雨,在无尽的寂寥中,回想着,漫忆着……
1978年,恢复中考了,我考上了重点高中。那一年,全县共收6个重高班,县中学2个,白龙中学2个,开封中学2个,三所中学“平分天下”的鼎足形势,足可见出两所区镇中学的地位和影响。我被开封中学录取,因此也结缘了开封中学的老师们。当时的校长是陈荣森老师,他一边做校长,一边上一个班的数学。开始是陈校长的夫人于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教我们数学。他们俩是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的同班同学,都是班干部,陈校长是班长,出身贫寒之家,而于老师出生在成都,现在的繁华地界熙攘闹市。因为恋人关系,因为共同选择,到了偏远的山区任教,扎了根。1981年,我考上大学那一年,陈校长调县中学任校长,仍然教一个班的数学。1985年,我大学毕业,到了县中学教书,陈校长和于老师的儿子正好读高中,我被分配教这个班,我便成为了我老师的儿子的老师,后来我们还成为了邻居。
说及陈校长教数学,他的表达不很连贯,是一种跳跃性思维,解题的步骤很简洁,反应快的同学很能接受,慢一点的,有些跟不上趟儿。当你要问相互环节上的关联时,他又重讲一遍,依然是先有的那种路数,“不就是这样的吗?”究竟是那样的呢?!只有自己慢慢体会和慢慢梳理了。相比之下,更多同学喜欢听于老师的数学课,比如我,初中的数学不怎么样,高中了,是于老师把我的数学兴趣提升了起来。于老师的课,是一种快节奏,容量大,有一种催逼的气势。常常举一反三,课堂上容不得你走神儿,也走不了神儿,听于老师的课,像是急行军。后来,换成陈校长陈老师了,慢节奏,深思考,跳跃性大,空白空间多,注重思维的深度和高度,虽然有点不适应,但尽量努力了听,努力了想,也就能跟上他的节奏了。于老师的课,是什么就是什么,陈校长的课,除了是什么,还有更多的为什么,很多同学常常在这个“为什么”上卡壳了。于老师的课,有感染力和召唤性,对听课者而言,启动力十足;而陈老师的课,理性,冷静,没有多于的话,语速上的沉缓或者停顿,也容易让听课的人走神儿,再回来,就跟不上趟儿了。记得还有一个月要高考了,陈老师对我说,“从现在起,不需要在数学上太努力,上课认真听讲,课堂上完成布置的作业,不把自己这以前学到的忘记了,高考不会很差的。”还说,“不要太焦虑,也不要过于紧张,从你的预选成绩看,考个一般性的大学是没有问题的。”那时,他常常用他的数学分析法,对参加高考的同学,总要进行一些预测性判断,几乎八九不离十。其实,这就是统计学原理,看各个学生的稳定性状况。尤其是对我的数学的单向性的要求和对待,对我后来的教学经历很有启发,那就是对于学生的针对性教学。
这个世界上,干净的人,纯粹的人,其实并不多。陈校长和于老师在方方面面所具有的口碑,是我今生少见的。他们出现和存在,让一些人感到亲近,也让一些人感到很不适应。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徒”,他们也常常被一些人远离和躲闪,他们的光芒太过强大。
再多的溢美之词,用于陈老师和于老师,都是多于。
他们一直在过着自己的生活,做着自己的事,没有多少冠冕堂皇的言语,也就依随了自己的心,做自己心甘情愿、心安理得的事。他们俩在工资提级时,究竟让过多少回?在职务的提升上,究竟拒绝过多少回?在面临新的楼房可以入住时,也总是让给别的老师去住,我所知道的,是两次。而他们,一直住在平房,没有固定厨房,没有洗手间。我也随着他们,每天都得提着个马桶来来去去一回。历史的档案,实际上也是当时的见证者的良心里,都有一本账。就是我这样的学生,被陈老师以校长的身份领导着,我也没有占过一丝一缕的便宜。倒是有人知道我是校长的学生,对我额外礼貌周至,而后来在陈老师调离后,却对我暗放冷箭,从此让我知道了人性人面人心的种种无常,在有些人那里,原来并不是一如既往的。
唯一的一次开恩,便是我夫人农转非。这在那个时代可说是天大的事,那也是市委副书记亲自签署在我的私人信件上的批文转至县委书记后的一个插曲,因为这事情也需要县公安局长的点头认可,陈老师说,“上次开县委扩大会,蒲局长专门跟我打了招呼……”凭这一点,陈老师觉得蒲局长会买他的账。陈老师,既是以老师的身份,也是以校长的身份,带我去蒲局长家,而且是大清早,蒲局长刚刚起床洗脸。适逢蒲局长女婿从外地回来,我们读大学时认识的,也跟我打了招呼。蒲局长很诧异,说“你们也认识?”陈老师和蒲局长三言两语后,蒲局长说,“你放心。我们讨论一下。”很快就有了好结果,我的夫人从农村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从此有了户口簿,有了居民粮。再后来,陈老师说,“我从来没有这么早去找过人”,这是真的。他就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纯粹的教书先生,纯粹的活在象牙塔的人,人世间的很多勾当,都与他无缘。我到了实外,有一年我们的结婚纪念日,独独请了调我进实外的老校长与夫人以及陈老师于老师夫妇,一是知遇之恩,一是教育之恩。那一顿晚餐,吃得很滋味,很酣畅。
念及陈校长的纯粹和干净,即便如我等声称“和光不同尘”者,汗颜啊!
不是我们非得要与时代俱进,而是时代总是挥舞着一根无形的鞭子,抽打我们,让我们成为了一种奴隶人生的行动者。想当初,陈老师和于老师是不让我报考师范院校的,要我报考财经学院,或者外国语,而我隐隐约约受了他们的影响,嗤嗤认为老师能影响一个人的心灵和灵魂,老师能改造一个人,老师能让一个人变好起来……这也是我后来“声讨”他们的一个歪理邪说的论据。我在那个“斯文不如扫地”的时代,确实“声讨”过他们,“是你们让我走上了人生的正途,也是你们让我走进了人生的陷阱”。当然,这也是玩笑话罢了。
清清白白,干干净净,质朴醇厚,公正厚道,他们做事,他们为人,他们夫妻相处,他们教育子女,没有不堪称楷模的。然而,时代的变化,也渐渐让他们醒悟。终于虑及自己子女的未来前途了。1988年,他们夫妇俩调到了广汉中学,一是于老师可以照顾自己的老父亲了,二是两个孩子的未来单位也能更好寻找了。到了广汉中学,一心只在教书,多次提升陈老师,都是拒绝,在广汉中学继续赢得“活雷锋”的赞誉。
这样的老师,这样的校长,都是一个历史的记忆了。
记得我调入成都时,陈老师对我说,“书教得好,也不要骄傲。和同事相处,一定要谦虚,还要人品好,人家才真正认你,服你”。这话,我是认可的,能把书教好,并不是什么大本事,能把人做好,才是一辈子的事。总的说,自从走上讲台以来,陈老师于老师和更多的我的老师,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不论哪一个方面,都是我的一面镜子。我一走上讲台,陈老师和于老师就把自己的孩子放到我的班上,是对我的信任,是对我的鼓舞,是对我的磨练。犹然记得,小小的县城,县中学是众目睽睽的,我任教的那个班,各级领导的孩子还真不少,副校长是教语文的,孩子也在这个班上,我的历史老师的孩子也在这个班上。至今想来,我没有额外了这些孩子的特殊对待,都是我的学生,都是一个教室里的学生,我做到了一视同仁,这不是我的无知,而是我的本心。再后来听到的各式各样的议论里,我也渐渐明白了,我的一视同仁,我的无差别对待,我的“人都是人”“学生都是学生”,竟然让我从站立讲台开始,就没有玷污了“教师”这个身份,更为重要的是没有让自己落入世俗的网罗。而这,大致也源于我的老师们的影响吧。
在那个比较贫寒的年代里,生活的温馨和浪漫,同样也贫寒了另一种光鲜。结婚的第一个纪念日,因为没有请客的钱,就自己双双动手,做点好吃的,而陈老师和于老师又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特地向他们敬献了我们的烹制。这不是什么奢侈,也不是什么腐化,而是一份心情,一份礼仪,一份诗意,青春的心开始在迷茫未来的美好憧憬,誓愿如他们一样恩爱尔汝、相敬如宾。也还记得我们夫妻俩吵过一架,气不打一处来,我把被盖掀翻在地,妻哭着告到我的老师那里,陈老师于老师被妻请进了屋。面对扔在地上的被盖,他们熟视无睹,就听我俩相互告发,一贯势如破竹的于老师竟然一言不发,只是听,而陈老师听完后说,“我听明白了,你们俩就是想过一种’相公请,夫人请’的生活嘛”。我还在固执中,妻已经破涕为笑了。于老师趁此说,“段增勇,还不赶快把被盖捡起来”,我便知趣地收拾起来。自此而后,我们没有再找过他们说长道短、判是论非。
于老师做过我的班主任,深知我的脾性,曾经对我的妻说,“小段是个认死理的人。”我知道于老师说的是什么事件,因为从那件事情,她看到了我的脾气,看到了我的倔强,看到了我的自尊。
如今,多想啊!好想啊!真想啊!
那一段回不去的时光,是满满的记忆,是满满的深情。
那一段逝去的时光,虽然是短暂的相处,入心入肺,深入骨髓。于老师未必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儿子,实在说,把我的妻当成了自己的女儿。上街买菜,喊着一路,不是为了陪伴,而是方便交流,交流夫妻相处之道,交流如何当好家属,交流如何避免是非,交流穿衣吃饭看家道……一个人的成长,不只在读书,更在生活,更在工作。我们曾经共同生活的那个大杂院,简直就是个小社会,现今回想起来,有趣得很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后来的一切,在那个时候的林林总总,都像是一根根丝线,贯穿着,连缀着。
我在西北的霜风里,我在望不尽的连绵群山的绵延中,我总想看见点什么,而恩师、老校长的最后一面也不能见见,我有些茫然。
听陈老师的儿子说,陈老师身前已经有了交代,并办了遗体捐献事宜,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我等学生们,也只是相互传递了这样的噩耗,也只能各自默然了心情,回想在我们的高中时代,回想着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份记忆。我看见“两袖清风”“清白人生”“廉洁奉公”“德高望重”“好老师”“终身难忘的恩师”“人生导师”等等表达,而我的感觉里,没有什么能像“干净”这二字,最贴切,最稳妥,最精到。
我急匆匆赶不上见陈老师一面,我在风雨的夜晚归来。一下飞机,雨水如注,我问成都那边,却说昨天一直下到今天。在这个半山亦景的酒店里,随来看我的几位同仁与我闲聊,听雨的心情,浸润了恩师的生命光辉,贸然间,“一个干净的人”,活跃起来,生动起来,让我的心砰砰然了生命的一种弦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永远都是自己的事情;做一个干净的人,是多么的不容易。然而,陈老师做到了,于老师做到了。他们从那个时代走来,固然也烙印了时代的印记,然而,在做人上的自律、自尊、自爱、自重,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没有理由不去努力的。他们在努力,我们也在努力,而我们,并没有挣脱丝丝缕缕的牵牵绊绊,虽不蝇营狗苟,却也常常成为熙熙攘攘中的一员,偶尔的醒来,也只是让自己的灵魂不至于彻底交给魔鬼。我们生活在一种苟且的状态,随流沉酣,追浪随喜,我们的坚持和坚守,是不很及格的。想到这些,出了汗颜,还有愧悔和羞耻。
今夜,我怀念一个干净的人,他是我的老师,是我的校长,而我们却一直称呼他“陈老师”。
他叫陈荣森,蓬溪人,剑阁开封中学数学教师、校长,剑阁中学校长、数学教师,广汉中学数学教师,这是他一生的职业和事业。从艰难困苦中走来,虽贵为省重点中学校长,却一直保持一名教师的身份状态,从不贪取一丝一毫,从不在名利争夺上动一点心思,从没存心伤害过任何一个人,那一颗初心,晶莹亮丽,那一份品格,高山仰止。
他,让过住房,让过提级工资,不是特级,不是什么突出贡献者。他,严于律己,仁爱待人,不争高下,不攀权贵。他,温良恭俭让—让人不让理;仁义礼智信—信实不信虚。像陈老师这样,一辈子没有干过坏事,一辈子没有因为校长而占过公家便宜,一辈子身为校长而没有公款吃喝,一辈子因为当老师却从不麻烦学生,一辈子管却自家身与心,一辈子清清静静清清洁洁,一辈子干干净净纯纯粹粹……
他,没有墓碑,也没有墓志铭,而在他学生的心里,在更多富有良心者的心里,有一座高耸的丰碑,铭刻着:陈荣森老师,一个干净的人。
试问这世间,能有几人哉!
此何人哉!
此何人哉!
2020年10月20日凌晨2点38分(转载 学生 段增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