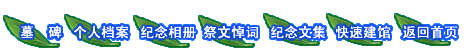那年的年夜饭我们是在病房里吃的,弟弟的岳父母给我们送来了丰盛的菜肴,但我们都咽不下去,端着杯子眼泪无声地流淌,这个家30多年了,还是第一次在除夕夜缺少了主心骨,爸爸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缘,唉,沉重的筷子、苦涩的酒,没有了欢乐,只剩下叹息和失神。
春节后媳妇回去了,当然把女儿也带走了,我留下来帮助妈妈照料父亲,反正新到一个地方发展,业务的起步也不是三、五个月的事。要说起抢救父亲的那家医院,在诊断和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方面经验还是有所欠缺,主要是因为我六姨在那工作,各方面照顾起来要方便一些。一开始的诊断是“蛛网膜下腔出血”,怀疑栓塞,因此多使用活血化淤的药物,后来由于持续昏迷时间太长,而我们所在的城市又没有CT等当时候比较先进的设备,只得去了趟长沙检查,结果确诊为脑溢血,这才开始对症下药,降颅压、收缩血管、吸收淤血、减少对神经组织的压迫。父亲逐渐从昏厥状态中摆脱出来,左侧偏瘫已经形成,也许是不适应、也许是神志受到一定的影响,他的右手格外好动,曾经在半夜把沉重的氧气瓶推倒在地,这让护士医生吃惊不小,说没见过如此暴戾的半昏迷病人,于是有一段时间,我们不得不从六姨父那借来手铐,把那只好动的右手铐在床沿边上,护士给他注射时也必须格外小心,弄不好就会一巴掌拍过来……
父亲完全清醒后,恢复的过程倒是很顺利,他很快就能在拐杖的支撑下开始学步,慢慢地学会了照料自己的生活,除了左侧完全不能动弹以及穿衣、脱衣这些复杂的动作外,基本实现了生活半自理,在某些情形之下,甚至可以不依靠拐杖行走一段短短的距离。想起一个小故事来,当时妈妈参加了一个退休干部的气功培训班,班上的学员们热情地要为爸爸发功治疗,盛情难却呀,于是某天晚上我只好带父亲去到练功现场,呵呵,那真叫一个群魔乱舞的场面,热腾腾的空气中弥漫着汗酸味,一个又一个热情地老头老太轮番为我父亲发功,呀呀呀呀地认真而尽责,仿佛要把爱心、气场和信念一咕脑地传递进入父亲的体内,在老人们的高声鼓励之下,爸爸很配合地走了一圈又一圈,最后为了早点回家,干脆放在拐杖在教室里走了一个来回!这下子彻底轰动了,掌声敢说响彻了云霄,气功的神奇与伟大在现场得到验证。于是这个奇迹与神话不翼而飞,那时大家都在传说一个瘫痪病人仅仅经过短时间的气功治疗,就丢掉拐杖走出教室,开始了全新的生活。爸爸听说后也乐了,说,他们太热情了,不忍心让他们失望,只好表演了一下……
其后不久,由于种种种种不便说明的原因,我和媳妇达成了协议,我还是回到湖南的那个县级市工作,至于户口和工作关系暂时放在武汉的那个郊区县。湖南有我的同学、有我的业务基础、有我的兄弟、有我的父母,我必须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
再不久,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父亲是退休干部,医疗费用倒是无需我们考虑太多,只不过是家庭历史陈欠太多,一直没能在经济上缓过劲来),妈妈支起了一个活动的小摊档,买点烟酒零食冷饮和小玩具,同时还摆了一张当时很流行的台球桌,5毛钱即可打上一盘,这个摊点出了院子大门大约还有7、80米,是一段坡度较陡的路程,每天早上摆出去、晚上收回来,一个带轮子的玻璃柜台、一个带轮子的冷冻柜,很重,推起来也很危险,台球桌是固定的,但晚上也必须做防雨水的处理。我和弟弟尽量帮助妈妈收拾摊子,那段日子,奢靡的生活方式得以收敛,这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懂得尽责、懂得分忧。又过不久,妈妈推出了新业务,编织毛线拖鞋,那式样、那款式绝对是当地的最新潮流,妈妈把它们拍成照片展示起来,一方面接受订货,一方面出售原材料,每天都有一大群嫂子们慕名前来学艺。我媳妇也算是个重情重义的人,虽然我们之间那时候疙疙瘩瘩、不尴不尬,她依然从武汉的汉正街帮我妈妈采购、进货、发货。也就从那时候开始,我有时间都守在妈妈的摊位上,一块一毛几分地帮妈妈收账;也是那个时候,我开始钻研业务,不再满足于做一个入门级的新手,我学习、我写论文,青春时期的作家梦终于实现——不是小说而是成为铅字的论文。几年的辛苦下来,这个摊子竟然成功地使我们家摆脱了经济上窘迫,细细一算,有了几万元的盈余。
爸爸那几年身体还算争气,尽管烟照抽酒照喝,毕竟没有再次复发。白天妈妈在摊上忙碌,我们要上班,他就自个在家看电视、看影碟,偶尔还自己拄着拐杖下十几阶台阶、穿过院子里的球场、再走上7、80米斜坡路来到妈妈的摊子前坐一坐、看一看,然后再原路返回。和爸爸同时或先后患同样疾病的周边老人,不是彻底瘫痪在床就是已经走了。爸爸的状况得益于妈妈的悉心照料,也得益于他自己不懈的锻炼,他那时说,我要活到2000年,感受一下新的世纪。2000年过后他又说,我要活到2008,看看北京的奥运会。
1998年4月,媳妇打电话来说,女儿下半年就要上学了,你在湖南也逍遥得差不多了吧?你看我们是不是……想一想,可不是?家里挺好,父母挺好,我也挺好,于是,那一年的那个月,我回武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