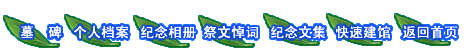妈妈的情况变化无常,比如我刚回家时她双脚冰凉,过了几天双脚竟然变得滚热,而手却变凉了。继而又发展为一只脚热一只脚凉。不变的是胸部以下除左手外全部瘫痪了,还有背部持续不断的剧烈疼痛以及没完没了、几乎没有休止的咳嗽。妈妈的精力几乎殆尽了,智力已经退化到了儿童的水平,不爱开口讲话,讲话时也没有任何表情,不论身边的人是被她逗得直乐还是辛酸得落泪都与她没有关系似的,她的精力或者说智力已经顾及不过来了。妈妈只要一开口就要说上一、两个小时——全是重复的话,加起来不会超过五句,一遍遍地在那自言自语,像一架破旧的留声机唱头卡在了唱片的纹路里,一遍一遍地重复、一点一点地跳进,比如她要表达的意思是:我现在也瘫痪了,才知道瘫痪是多么痛苦,可你爸爸却瘫痪了十四年,不容易啊!她就会一直这样说下去,直到其中一句或几句发生了改变,她又会接着改变了的话继续重复,到最后,那意思可能就成了:不容易啊,瘫痪不容易啊!挺伤感的场合,却弄得你忍俊不禁。我就一直在揣摩,妈妈可能并不清楚在说什么,她只是大脑机械地重复运动着,驱动着声带发音。
六姨告诉我,我没回来前,妈妈说,让大崽快回来啰,我有好多话要交待他!等我回来了她却什么交待也没有了,在她看来儿子回来就齐活了,也许在她蒙浓的意识中,我就一直在她身边。这时候的妈妈已经将经历了67年人生的记忆大门在自己身后缓缓关闭,除非外人刻意地追问、反复地催促,她才会从最后的缝隙中找出一点什么来,对妈妈而言,生命的全部的意义仅仅是她迷蒙的目光所能触及的几平方米的世界。这样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质量可言,仅仅是苟延、仅仅是残喘、仅仅是维系、仅仅是存在,假若,国家的法律允许安乐死,作为长子我会替妈妈选择体面而有尊严地离去,我不愿意看见自己亲爱的、熟悉的妈妈成了这个样子,让游丝般的生命被病魔一点点占据、侵蚀、分解、吞噬。
其实妈妈很好护理,白天六姨都会来,给她打针、换导尿管、擦拭排泄出来的污物、擦身体、清洗口腔,有时还要洗头,有些工作我们做儿子的不方便做,六姨都承包了,要知道那种气味实在强烈,尽管是自己妈妈,我在一旁协助时也难免会有要呕吐的感觉,六姨却眉头都很少皱,我们兄弟都挺感动的。剩下的时候,妈妈唯一的动作就是用仅有的一只手转动窗帘布,然后将卷成一团的窗帘布贴在自己发烫的脸上,松开再卷,周而复始,或许这样能让因发炎而肿胀的左脸感到些许凉意。疼觉袭来时,妈妈就会变得不安,嘴里开始哼哼,甚至身体也会试图扭动,一会要求我们扶她坐起来,一会要求我们把她的脚高高抬起,要高过她的头顶,她根本就没考虑这个年龄还能不能做这样的动作,也没有顾及自己下面没有穿任何衣物,事实上抬起她的腿她压根也没有感觉,即使眼睛看见了也不会认为那是自己的腿,这个时候我们就给她注射杜冷丁,杜冷丁见效快,吗啡呢见效慢但维持效果长,这就需要我们根据情况决定。说实在的,我们一直困惑,妈妈的表现究竟是病疼的折磨呢还是毒瘾在发作?都像,或者兼而有之吧。
妈妈也不好护理,首先她的烦躁并没有规律可循,可以是上午,可以是下午,也可以是夜间任何时间段,我和弟弟睡一张床,就在妈妈的小床旁边,兄弟俩轮流守候,可毕竟我休假在家,弟弟第二天一早都要出车,在接近年关的时候,为保障春节期间的血液供应,采血任务非常繁重,通常是下农村采集,有时一天要采上百个血,我看他只要脑袋一挨枕头,立马呼噜连天响,很少有超过5分钟的时候。当妈妈后半夜发作时,我只能坐在妈妈床前,一边轻柔地抚摸妈妈的脸颊一边轻声地哄她睡觉,妈妈倒也听话,可就是持续不了几分钟,看情形说好话没用了就喂她吃吗啡,如果吗啡还不能解决问题,就只能叫弟弟起床打针了。有天夜里打完针后仍然无效,只得叫弟弟起来再打一针,结果这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也没醒,把我和三姨吓得不轻,每隔几分钟就轮流过去看看,观察妈妈胸部是否还有起伏、鼻孔是否还有出气,不过后来六姨说了,剂量是大了点,但还在许可的范围之内。
说妈妈不好护理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吐痰。肺部感染必定会产生痰液,可问题是妈妈已经虚弱到没有能力完成清清嗓子、吐吐痰这样动作了,换成正常的人,喉咙里的那点痰也就是清个两三次嗓子就处理干净了,妈妈却要花上一个小时的时间,而清出来的可能连淤积总量的十分之一也不到。妈妈要积蓄数十次的努力才能让肺部产生那么一点点的推力,把喉咙里的痰外推动那么一丁点,光听见喉咙里呼哧呼哧作响,把我们急得呀!又帮不上忙,只能配合妈妈的动作用手掌推压她的胸骨部位,期望施加那么一点动力;或者把妈妈扶坐起来,拍打后背;再或者让妈妈侧身,让口腔的高度稍稍有所降低,而手里还要用纸巾不停地擦拭,一次吐痰短则半小时长则一个钟,丢弃的废纸几乎要装满半个纸篓。
每天上午和下午,父亲会要求把他推到妈妈床前,他要陪陪老伴。父亲用唯一能动的右手伸进被子抚着妈妈已经瘫痪的右手,父亲不能说话,妈妈不愿说话,两个人就这样对视着无声地交流,隔不久父亲就开始抽搐,肩膀和身体发出剧烈的抖动,这是父亲在哭泣,他失语了同时也失去了放声痛哭的能力,有时妈妈也会淡淡地说一句:普文同志,你不要哭了!仿佛今生来世早有约定,不再需要更多的语言。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在父亲苍白的头顶,形成一种剪影般的光晕,这对都不能动弹的老夫老妻,就这样默默守候着他们今生最后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