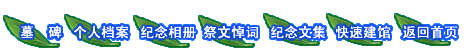那天下午5点,所有人又回到了我家,楼下的保安吃惊地张大了嘴。奶奶的情况比预想的糟糕也比预想的要好,糟糕是因为经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诊断,奶奶头部左侧多处头皮裂伤,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和擦伤,右侧第九肋肋骨骨折;比预想的要好是因为一个百岁高龄的老人如此一番折腾竟然只落下这么点“小伤”,北京的亲人在得知检查结果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原以为这么一摔即使不断三、五根肋骨也得折条胳膊断条腿或落个盆骨骨折什么之类的。比起奶奶受伤,我们更不愿意看到的是四姨也是左侧第十肋肋骨骨折,人家可是来帮助我照顾奶奶的啊!刚走几天的四姨父又赶回深圳,经紧急求助,三姨放开家里的一切赶来深圳救场,担负起照顾奶奶和妈妈的重任。几天后,四姨夫妇不忍增加我们的负担乘车回家养伤去了,四姨走的时候,奶奶抱着她痛哭,她心里有点愧疚,总认为四姨的受伤是受自己的连累;四姨走的时候抱着我妈痛哭,我知道那是姊妹难舍之情,四姨知道此去恐怕难有机会见到妈妈了;四姨走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沉重,她是为我们家的事受的伤,我也请律师去与深圳地铁交涉过,希望能得到一点赔偿,可是地铁方面拒绝了,我只能看着四姨捂着肋骨空手返家。
妈妈此时咳嗽加重并有背部酸疼的感觉,我清楚地知道,这是癌细胞扩散压迫神经造成的,妈妈的日子可能不多了。我们总是变着法子哄妈妈:这肯定是吃药造成的,那“神医”的药不是说化疗的作用吗?痛表示药物正在杀癌细胞,是好事!妈妈对自身的变化还是有数的,有点不相信地自言自语:难道这么快就到中期了?哪能啊!我有时很佩服自己胡诌乱造的本事,书上说了,只要适当加以控制和治疗,早期进入中期,至少需要三年以上的时间,至于中期进入晚期,也不是一两年的事,你应该看到很多癌症患者吧?人家进入晚期还能活个三、五年的,活十年以上的也不是少数!您啦,别疑神疑鬼的,一点酸痛,和你的癌症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事!
话虽如此,我还是决定带妈妈去做CT检查一下,一是看看那些药丸到底有没有效,二是证实一下那该死的癌细胞究竟扩散得怎么样了。结果CT显示,肿瘤略有增大,不妙的是有向肝脏转移的迹象。抽了个空子我找到医师,把妈妈的病情如实相告,拜托他坚持属于早期的判断,这是个富有医德且经验丰富的医师,他很赞同精神支撑赛过药物治疗的观点。于是向我妈妈煞有介事地讲解了一大堆专用术语和名词,巧妙地把已经增大的肿瘤说成是形状发生变化,大小变化不明显,对于肝部的阴影则闭口不提。
好不容易把妈妈安抚下来,爸爸的情况又恶化了,从起初的发音略显含糊到吐词不清到基本失去语言功能,流口水则发展到了泛滥的地步,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父亲的这些变化不是休息不好也不是抽烟喝酒造成的,而是很有可能颅内再次血肿或出血,压迫了相应的神经。CT检查果不其然,新的出血区域、陈旧的区域交错横亘,让拍片的医生吃了一惊:脑子里都乱成这样了,这位老先生还安然地坐在轮椅上抽烟?接诊的女医师用命令的口吻要求我们立即办理住院手续,对此我和妈妈相视苦笑,只是请求医师开些降颅压、降血压的药物,我们回家慢慢调理,女医师断然拒绝,并用一种极其蔑视的眼神盯着我,目光中分明在谴责:你这个不肖子,难道就这样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亲死去吗?你的良心何在?难道几个臭钱就比父亲的性命还重要吗?我有口难辩:住院?你以为只有父亲需要住院?我妈是癌症晚期,家里还有一个骨折的百岁奶奶,她们哪一个不应该住院!可是,难道要我把整个家都搬到医院来吗?父亲连上厕所都需要人背,我纵有三头六臂也应付不过来呀!我还有自己的工作吧?女儿也需要我照料吧?况且……况且那时我经济上也的确山穷水尽了,这几个月来,每月开销均在万元以上(这还不包括房屋的按揭和媳妇为这个家庭花掉的钱),我实在没有能力承受下去了。有时候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望着车水马龙的滨海大道,真的连找根绳子把自己吊死的心情都有了。
俗话说久病成医,那个女医生不开处方,我们就自己去药店买药,不就是抑制颅压和血压吗?妈妈伺候了爸爸14年,该用什么药早就烂熟于心,结果一个星期下来,父亲的症状就控制住了,但是神经的死亡是不可逆的,他的语言功能算是到了尽头。不过迄今我也没有任何怨恨那个女医师的意思,至少我知道,她是个讲孝道的好女人,她考虑的并不是医院的经济收入,而是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
8月30日,奶奶在三姨的护送下再次启程返京,这次平安顺利抵达。两天后三姨从北京直接返回江西,留下的约定是:等她把家里收拾好,让爸爸妈妈去江西养老,他们两口子在自己家里尽心尽力地伺候我的父母,满姨也在江西,还是当地职工医院的护士,虽然刚刚办理退休手续,但医院的资源还是搬得动的。经历过这场风波,我也失去让父母一直呆在深圳的意念,一是精力二是经济,我明白万一父母任意一方再来一次病变,我或许真的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受难了!
2006年9月26日,父母离开了仅仅生活过三个月零六天的城市,离开了他们自己长子的家去投靠自己的妹妹!妈妈临走时留下了自己夏季的衣物和一千块钱,说等过了这个冬季,明年开春了她再回来,抱着这堆衣物我哭了,我知道,妈妈再也没有回来的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