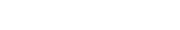短忆黄颂杰先生
胡云峰 2020/3/12 14:27:00 浏览:326
昨天早上从朋友圈看到汪行福老师发的消息,心里还是暗暗吃惊,知道他晚年身体不太好,但是在这个时期仙逝,还是没想到。想写点什么,可一时又无法动笔,因为对他了解甚少,只是为复旦当年外哲“元老院”走了这么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感到非常惋惜,正是出于这种敬意,我才敢冒昧动笔,以抛砖引玉。
约摸三年前我参加了复旦的一个学术会议(会议主题是讨论俞吾金先生的启蒙思想),聚餐时我恰好和黄先生一个桌子,整个桌子都是非常安静地就餐,就是讨论,大家也都压低着声音。当时我与黄老师只是象征性地彼此用红酒隔着空气“碰”了下,这时我才发现他的手有点抖动,已经不似十年前了。
昨晚凌晨临时脑补了下朋友圈中疯传的他的自述,这才使我对这位可敬的老师的家族背景和人生经历有了些更多的了解。
首先我在想对于哲学大师的仙逝,我们应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对于生与死抱何种态度,这是一个根本问题。著名哲学家伊壁鸠鲁在去世前还让仆人给他泡个温水澡,而皮浪则要求人对于危险应该抱着一种糊里糊涂的态度;一句话,哲人对于死亡不应该是错愕或叹息、而应该把它理解为回家,一个从那里诞生的家。
这个过程可能会有惊险,比如病痛的折磨、亲人的无能为力、焦急失措、医生的放弃等等。据汪行福老师说,黄先生由于是疫情期间送到医院去的,所以,家人、学生都无法亲自送他最后一刻。这的确是遗憾,但这又是“命”——俞吾金先生讲的那种“倔强的偶然性”、“打破常规的偶然性”。
其实昨天我从朋友圈一共收到两个噩耗,还有一个是岳西的一位微信朋友发消息说,他的一个表妹才25岁,也于昨天因病英年早逝,相比较,这更加是命运无常的表现了。碰巧的是,今天傍晚我的楼上也走了一位,是几楼、是谁目前我一时还无法搞清。
所以我对哲人的离去更愿意去关注他的思想或曾经怎么思想的。但是黄先生真是一位很低调的老师,我在04-07年间在复旦读书时,他已是60多岁的半老人了,所以我在复旦期间,未见他开过什么讲座,发表过什么演讲,主要的见面机会就是上西方哲学史的大课,这个课是由黄老和其他几位“元老”一起合上的。
黄先生给人的感觉最大的特点是率性、随意,但不凌乱。想想,六十多岁,一头银发,上身经常穿件西装,走路轻巧快活;说话也快,铿锵有力,从不看草稿。
他上课还有一个特点,说观点比较稳妥,不是那么把话说死,总是带着商榷的语气。我可以举出他2015年和俞宣孟先生的对话为例(见划线部分):
很多现代西方哲学家严厉批判了传统的思辨形而上学,有的人认为形而上学已经彻底终结了。这种讲法恐怕是有问题的,传统的形而上学可以否定(实际上现在还没有完全否定掉),但形而上追求否定不了,否定形而上追求,也就否定了科学。而有形而上的追求,就有可能产生形而上之学。
黑格尔以后的西方哲学,通常被称为“现代西方哲学”。所谓“现代哲学”,这个转折不是 19 世纪中叶一下子完成的,甚至到现在这个转向也未必就完成了。国内学术界有一个看法,好像是尼采完成了这个转向。我觉得,这个看法有问题。比如,20 世纪的哲学家,罗素和胡塞尔,他们也是要寻求知识的根基或基础,这种追求还是很传统的。传统并没有那么容易断裂。尼采是开始而不是完成了“转向”。(开端、目标与普遍性——关于西方哲学的对谈.黄颂杰俞宣孟.哲学分析.2015 年第 4 期)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出黄先生为人虚怀若谷的特点。表面上看,他好像不是很确定,但其实这是一种委婉的确定,让人很容易接受。所以在他身上,我们好像没有看到过哲人之间的那种争锋“论战”,这种委婉与俞吾金老师论锋逼人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
3
黄先生自述自己一生研究都是“打游击”,教到哪里,研究到哪里,没有专攻方向和稳定的路线图,这也与俞吾金老师在80年代就严格制定好自己的专攻“计划”形成对比,但是这种无计划的“表层耕耘”,也有一种不明显的优势,即不会钻牛角尖,到哪里都能带着“元问题”。在他人生晚年,带着思辨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他重回到古希腊经典研究。重回哲学的开端,这或许是他一生读书研究的最大心得,而这份心得或许将影响整个哲学场。
下面是他2014年对杨国荣教授实践哲学观的答复,从中我们可以琢磨出他的视角为何:
实践哲学须解决三个问题:何谓实践哲学?实践哲学是否要取代思辨哲学?实践哲学有没有一般(或基本)原理?
实践哲学有双重含义:作为哲学的性质、形态,与思辨哲学相对;作为知识学科的名称,与思辨哲学中的第一哲学、本体论和知识论相对。可以从与思辨哲学相对的意义上理解实践哲学。
思辨和实践同是人类生存状态的两个方面,思辨哲学和实践哲学有发展先后和成熟程度之分,并无地位上的高低优劣之分。传统思辨哲学经历长期发展,有过繁荣辉煌的历史,如今已走向式微;实践哲学正在蓬勃发展之中,但并非要取代思辨哲学。实践哲学并不排斥理论或思辨,无论作为哲学的性质还是作为知识学科的名称,实践哲学都需要自己的基本原理。 (黄颂杰.关于实践哲学的三个问题——从杨国荣教授新著《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说起,哲学分析,2014年第2期)
至于黄先生晚年对完善学术管理(这个问题在最近几年屡屡成为热点问题之一)发出的恳切呼吁,这也许是他担任《复旦学报.文科版》主编后的深刻体会。他有一个观点是振聋发聩的,即中国的现代化除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还必须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化,而这两者都要求有一个健全的学术管理体制和机制。
中国要超越西方发达国家走到世界现代化之前列,就必须在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思想领域占得先机。...关乎学术研究成败功垂的学术管理,应从现代化的实践中建立起真正推动和促进学术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学术管理中的意识形态、权力和功利.云梦学刊.2012年04期 )
至于黄先生建议具体如何改进当下学术管理体制,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
最后让我们再次一起聆听黄先生自己对人生的体会:
从我1957年进复旦大学哲学系学习到2017年正好一个甲子,六十年。我对这六十年的一个总的看法是四个字——“平凡人生”。我是一个平凡的教师,平平凡凡。这不是我谦虚,而是我感觉到这是对我自己六十年真实的写照。因为我这个人一生追求平凡,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要成为一个什么卓越的人物、伟大的人物或者什么高大上的名声等等。我没有这么想过。
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讲得比较响亮,譬如“追求卓越”就是很响亮的口号。我觉得,这个口号对我来说不怎么心动。我不是反对追求卓越,我觉得追求卓越还是非常好的号召,但是我衡量了一下自己的能力、智商和各个方面的条件,我感觉我做不到这点。我只能做平平凡凡的事情。
但是六十年来,我常常感觉到事物的真相,这是用我们哲学的语言来讲,事物的真实面貌,在平凡的地方最容易显露出来。平凡之处才显露出事物的真相来,平凡之处才能见真理。(哲学是一个问号——黄颂杰自述.实践哲学评论(第四辑))
也许,我们应该记住这句教诲:平凡之处才显露出事物的真相来,平凡之处才能见真理。真理不光在高伟的报端墙头,更体现在社会的每一个具体的神经末梢。
黄先生千古!
- 暂无评论!
- 发表评论文章评论(共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