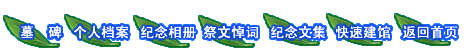说到鄂尔多斯的街头小吃,我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碗坨。这种食物,做法大概是荞面加水,上锅隔水蒸熟。冷却后切块或条状,配以自制调料汤汁(类似搭配凉皮凉粉的调汁)。
在这里吃的第一顿饭,满满一桌子菜中间一大盆毫不起眼的,就是碗坨。
亲戚特意与我介绍,此为本地特色,在我家乡是没有的,热情招呼我下筷。我见它卖相不过尔尔,兴趣缺缺,但终究不忍拂其好意,夹了几块入口。口感类似灌肠,或者说,像凉透了的浆糊,稍比浆糊结实两分。调汤味道亦十分普通,似是酿皮里调汤的下脚料,兑了些凉水敷衍了事。论口感,输给酿皮的筋道,逊色于粉皮的清爽,至于汤料味道,层次变化不如凉皮的丰富。实话实说,我之所见,乏善可陈。这是我对碗坨的第一印象。初次见面,几乎就要盖棺定论。其后亲友如何劝说,不再下箸。
后来的几年里,时常被交好的本地朋友拉去街头吃碗坨。街头的碗坨,顾名思义,是碗里浅浅薄薄的一层,用刀划开,浇上汤汁佐料,用细细的长竹签扎着吃。我抱着"兴许上次吃的不正宗,再试一次"的心态,尝试了数次。然而每次都会不出意料的失望,渐渐的,对这种食物彻底沦为路人感。无奈盛情难却,虽不以为然,每次受邀仍欣然前往。只是不免腹诽鄙夷:大抵是东胜人没吃过什么精致的食物,竟对如此寻常无奇的小吃趋之若鹜。
对碗坨的"歧视",一直持续很多年。直到前些年的某天下午。
几个要好的同事相约翘班偷溜出去。出门不远遇到推车卖碗坨的,同事们纷纷驻足,争相请客做东。我忍不住翻了老大的白眼:走罢!又是碗坨,有什么好吃?转头看时,几个人已经端着碗。其中一人抱怨:碗坨涨得这样贵了,居然要两块钱一碗。小时候不过一毛钱。卖碗坨的大娘笑着解释原材料涨价连炭也涨了不少。我不耐烦诸君时间浪费在此,催促打断:这东西涨到多少钱我都不稀罕去吃。不晓得你们本地人吃没吃过好东西。
有个姑娘并不生气,缓缓道来:"现在确实不算什么好吃的了。小时候不像现在,街上没那么多花样小吃,也没什么零花钱。我上小学时有次攒了五毛钱全部拿去吃碗坨了。站在那冷风飕飕吹,但是觉得好满足。长大了,好吃的东西多了起来。我知道碗坨不是最美味的,可是只有它会让我想起我的童年。与其说吃碗坨,不如说是在回忆过去,所以吃的也就不仅仅是碗坨了。"说完挑起一块荞面,她轻轻笑了笑:"这大概就是人们说的一种情怀吧。"
一语惊醒梦中人,醍醐灌顶一般。其实口味这种东西,本来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口难调,因人而异,实在没有办法定个标准评价出高低优劣。我不也一样有很多钟爱的事物,别人看来不值一哂。我视心头好,旁人当作草。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我们对于某一种食物,某一种味道,某一段旋律,某一部影视剧,某一类活动,某一个人,有特殊的好感和情结,无非是他/它们身上承载了某一段时期深刻而又美好的记忆。被承载回忆的他/它们,像是一把打开往事的钥匙,一串密码。轻触机关,推开记忆的闸门……呵,弥足珍贵,往事难忘。
有些人会羞于承认曾经热衷痴迷的物事,因别人无关紧要的想法和评价,渐渐生出嫌隙,甚至与之划清界限,弃之如履。此辈为我所不齿。思及往日种种,如脚下烂泥,恐污其身,避之不及。可有想过,曾经也是为之欢天喜地过的,心性该有多凉薄?当你对曾经摆出厌憎的面孔,你厌憎的是你自己。与"过去"反目,是一种打脸式背叛。我欣赏一种人,不否定自己的过去,不嫌弃,不诋毁,不对旧日所爱口出恶言。我对其肃然起敬。或许多年后的某天回头看,其实不过如此,归于寻常,可我仍愿惦着你的美好。没有什么能取代记忆中的你……
此后,我再没有对碗坨"出言不逊"。偶尔,我也会在街边稍作停留,叫上一碗。口感口味仍旧不喜,但我尊重某些人如珠如宝般的记忆和情怀。
如果可以,我好想穿越回去轻轻拥抱一下那个当年在寒风中吃碗坨的小姑娘。
From身沾世俗烟火色,心藏长街千堆雪的周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