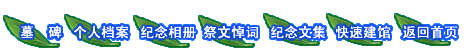落笔之时,我已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脑中各种纷乱的念头。
今天是二〇二〇年二月九日,我的高中同学程容然猝然离世的第五天。从医学角度而言,“猝然”这个词似乎并不准确,他的病程,总有三、四个月之久吧;可我还是只能用“猝然”这个该死的词来形容他的离开 ……
大家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个周四的晚上。有同学自上海来汉,武汉这边临时召集几个同学在洪山广场附近聚一聚。程容然从东西湖出发,开车到长青路接老师,再一路堵车开到武昌这边,应该走了二、三个小时。他一直是这样,别人做得更多,却不以为意。
就是这一次,他和我说起身体的状况,提到手术之后诊断不明确,跑了几家大医院的肿瘤科和血液科都没法最后确诊。
“我现在挺好的,没什么不舒服,每天还在跑步”。最后他说。
身为医生,心中很明白一种疾病迟迟不能确诊往往不是好兆头。我只能说,“多注意身体,还是往血液系统方面多查”。
那天第一次看见他没喝酒,就喝茶,可是离座给大家倒酒的样子,依然是班长风范,诚恳毋庸置疑。
其实我们的交集仅仅限于高中三年短暂的同学时光,文、理科分科之后,我们还曾同桌一段时间。可是很多具体的事情和细节都已模糊不清,因为此后漫长岁月的纷杂琐事掩盖,更因为年少时的漠然。关于他的名字,他解释来源于《红楼梦》,可是至今《红楼梦》已翻了几十遍,还是没有找到答案,只能以后再找他求证了。还有一次到学校寝室卫生大检查,
“有人床单一个学期都不洗!”我一直记得他说这句话时脸上单纯的深恶痛绝的表情。另有一次体检,测完体重之后他唏嘘不已:“十斤啊!那是多大一堆!这么长,这么宽……”他边说边用双手比划,仿佛在评价搁在案板上的一块红白相间的肉,圆脸上笑得很开心。
再见,已是二、三十年之后。我们都已从少年跨入中年的门槛。他作为周黑鸭集团的生产总监调至武汉,武汉能找到的同学第一次聚在一起,那是二〇一八年的十二月十五日,星期六。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
看起来,他和高中时候没有太大变化,不仅仅是外貌,还有对事对人的认真态度,喝酒时的豪迈。
以后的联系都在微信上,武汉的小群里大家偶尔你一言我一语瞎辩几句。又一次私信我,咨询医学方面的事,却是个沉重的话题,他没有急躁,也没有抱怨,只是很客观的问了些问题。
最后一次联系,是看到他在群里的消息,协和住院,回到京山接着住院,感染、血小板低……到了二十三号,我毕竟还是忍不住私信他:
“啰嗦一下,你的情况不排除血液系统问题,自己要当心,别耽搁太久。”那天下午我自己肺炎确诊入院,再无暇他顾。
现在回想起来,他是否心中早已明白,只是不愿意打扰大家?或者说,我们愿意让他明明白白地离开,还是希望他浑然地长眠?我们无从了解他在疾病困扰的身心煎熬,也无从了解他对人生人世不舍却不得不舍的身不由己。可是我还是愿意相信,他是心地清明而平和地走进另一个世界的,正如定格在记忆中的笑脸。只是,只是走得实在太早啊!
这个冬天,如此艰难。
谨此,纪念我的高中同学程容然。班长,一路走好。
2020.2.9 23:09
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