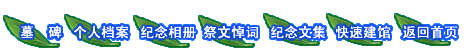怀念母亲(五):心系故乡,亲情至上
我母亲在家排行位六,从小深受姥爷姥姥、姐姐哥哥的关爱,在温暖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故乡的田园小河、亲人的音容笑貌深深地印刻在她的记忆中,陪伴了她一生。
1953年我母亲自扬州财经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参加工作,1957年与我父亲结婚前,经常回泰兴探望姥爷姥姥和姐妹兄长。据三好姐回忆,我父母结婚后仍经常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回去看望姥爷等亲人。1958年我在南京出生,1960年小东在大同出生,1961年的3月份父母亲带着不满3岁的我,从大同回泰兴姥爷家看望亲人,三好姐清晰的记得我兴奋地在外公的田园里游览,一起在田园里玩捉迷藏。1962年春兰出生,1964年秋兰出生,再加上跟随父亲调动工作,母亲回老家的次数少了,她对家乡亲人的思念越发深切。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姥爷受到冲击,舅舅和舅母也从城里下放到七圩学校工作,在泰兴的几家人都是早晚喝粥,中午吃着稀糊菜面。了解到家乡亲人的艰难处境,我母亲焦虑万分,冒着受牵连的风险,将自己省吃俭用的钱寄到大姨家,再由大姨转送到姥爷手中,直到1983年姥爷去世从未中断。大姨父由于遭受造反派的毒打,一病不起,很快去世,大姨也因担惊受怕、营养不良、劳累过度病倒,血小板急剧减少,浑身布满紫血斑块。我母亲接到年仅14岁的三好姐的来信,迅速汇款寄药。小姨上大学期间因医疗事故造成耳聋而辍学,心理受到极大打击,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我母亲通过写信、寄钱、让小姨来家里住、陪小姨到北京游玩、安排大女婿送到南京家中等多种方式关心帮助小姨。受母亲的感染,1991年3月我去南京出差时,专门带上照相机和三脚架,抽出一天时间去看小姨。当母亲看了照片、听完汇报后,我“遭到”了表扬。我和弟妹们深知母亲对家乡亲人的感情至深,对泰兴亲人遇到的困难,母亲是有求必应,尽力帮助。
我第二次随母亲回泰兴是1970年,那一年的8月我父亲调任丰润县武装部,母亲、奶奶和我们几个孩子大概在10月份从临汾举家搬到丰润,母亲在正式上班前,带着我、小东、秋兰于1970年11月踏上南方探亲之路,我们先后去了南京小姨家,上海二姨家,从上海乘船到镇江,在镇江坐长途汽车到泰兴,换乘小木船摇到泰兴,就住在大姨家,平生第一次吃到菱角和咸味蔬菜馅汤圆。三好姐的成熟、为民的淘气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972年2月爱兰出生,年底我参军,由于母亲是一个对工作特别敬业的人,从不因家事请假,单位也没有年假。回泰兴从此就变得困难了,好在母亲一直保持着和姐妹兄长之间的书信联系,大姨、小姨、光太、光华等陆续北上来到丰润住在我家,也使母亲的思乡之情聊以慰藉。
我母亲对家乡亲人的感情很深还表现在关心每一位亲人的情况,经常讲起家乡的亲人如何有学问、有能力,时常翻看老照片回忆当年的情景,每次收到家乡的来信都反复阅看,每当有泰兴晚辈考上了好学校、取得了好成绩、安排了好工作、事业上有进步她都兴奋不已,津津乐道与我们分享。每当有亲人故去,都令她伤心难过,独自静默许久。大姨去世时我刚好在家,目睹母亲不吃饭把自己关在卧室哭了一天,悲痛之情令我们动容。
1988年退休后,母亲多次表达想回家乡看看的愿望,考虑到健康和年龄等因素,我们不放心她单独回去,但各自的工作和事业正处于打拼期,家中的孩子也还小,总觉得以后机会很多,以至于最终没能成行,这也成了我们心中的遗憾。
2009年春天母亲患病来京治疗,同年10月份光平姐、三好姐和二位姐夫曾到医院看望,荣成哥、光太哥、三好姐先后去家中看望母亲。每次看到娘家人母亲都激动不已。2019年随着病情的发展,母亲经常昏迷,已不能说话表达,当听到三好姐用家乡话呼唤时,她被久违的乡音唤醒,紧握着三好姐的手,眼睛闪着泪花,令我们惊叹不已。
母亲离开我们走了,至此,姥爷姥姥的七个子女——母亲的姐妹兄长都走了。我们应该学习和继承他们修身齐家、自强不息、亲情至上、互助互帮的美德,延续上一代人的亲情并传承下去。
(感谢三好姐、光平姐提供泰兴亲人的情况!)
小宁
2022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