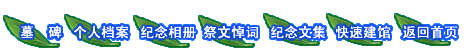怀念母亲(三):南方人改吃北方面食
我母亲是江苏泰兴人,出生地唐家港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饮食习惯和北方有很大不同,可以说母亲是吃大米长大的,和我父亲在南京结婚成家二年后,就跟随父亲的调动到山西大同工作。山西产小米、莜麦等杂粮,大米就成了稀罕物。后来我们又跟随父亲到了临汾、河北唐山丰润。在计划经济年代,粮食是按月定量供应的,居民口粮的品种以当地的粮食作物为主,国家调配为辅。南方产大米,北方产小麦、玉米、小米等,所以,南方定量中大米多,面食少,北方则是面多,大米少。那时候每个城市居民家庭除了户口本还有粮本,只能凭粮本和粮票在粮店买到粮食,根据每个家庭成员的年龄、性别、职业不同,规定可以买多少粮食和食用油,又把粮食分为粗粮和细粮,按比例供应。玉米面小米算粗粮,占比多,大米白面算细粮,占比少。我父亲是山东人,爱吃面食,特别是煎饼。我印象当中,在临汾,奶奶和我们同住,总念叨想吃煎饼,但临汾是山西口味,小米、玉米面、莜面多,街上、饭店里没有卖煎饼的,商店里也没有摊煎饼的工具——鏊。因为吃不上煎饼,我奶奶有时候说气话,要回山东老家。我父亲是孝子,托供销社的人出差从山东带回来一个。鏊是生铁铸造的,形状是圆的,表面是平的,打磨的很光滑,直径大约有70公分,厚度大约有2公分,有三条腿支撑,高约12公分。当时我7岁左右,感觉鏊非常重,是二个战士抬进来的,原有的灶台放不下,只能放在地上。奶奶看见鏊来了笑容,做煎饼时,只见奶奶坐在地上,在鏊下面烧柴把鏊加热,在表面抹上薄薄的一层油,用勺子把糊状的玉米面倒在鏊上,用刮板迅速把糊糊刮平,稍后再翻面继续加热就做好了。奶奶每次都做很多,摞在一起放着当干粮,每次吃的时候放在蒸屉上加热就可以上桌了,由于是用烧木材加热,满屋子烟雾缭绕,摊出的煎饼都带有烟味。奶奶和父亲吃的津津有味,我们几个孩子有一半北方人的基因,刚开始吃觉得新鲜,后来天天吃、顿顿吃,时间一长,我真的吃腻了、吃顶了。那几年,我把一辈子的煎饼量都吃完了,以至于后来见到煎饼就躲。我每次回山东,老家人拿出最好的煎饼招待我,我总是找各种理由不吃。我一个在北方长大的孩子尚且如此,母亲是南方人,吃惯了大米,她的感受可想而知。但是,我从未听到母亲一句怨言。
小宁
2022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