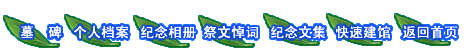老家 童年
我的爹妈,当有了我这个女儿后,视我为掌上明珠。当又添了两个弟弟后,生活不宽裕,我就不那么幸运了。当我记事到1949年前,家里被土匪抢了三次,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了,家里一贫如洗。家里四口人的衣服都被抢走,三次遭土匪,父亲都出门了。他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走山串乡卖点针头线脑,换点吃的送回养家糊口,就这样直到49年全国解放。至今记得我有一件漂亮的绣花小肚兜,平时妈妈不叫穿,过年过节才穿几天,叫土匪抢走了,真心疼。土匪有一次来了, 忙着抢东西,连马匹也牵进屋里,用枪托向母亲身上戳,大喊:“有洋烟没!有就快拿出来”。母亲说:“没有”。于是那土匪就到处乱翻,见包就拿,往马背上的口袋里装,就连磨刀石和剃头刀全部扫走了。全家就数父亲的被子好点儿,也抢走,连母亲的小脚鞋包,也没幸免,我躲在炕上吓得大哭。
有一次土匪进屋前,我正好去找叔伯小姑姑玩,走在五字湾村北口,就见一群牵马的人,正听一个人喊话。我有了小经验,断定是土匪,我回头向家跑去,去给妈妈报信,母亲赶快抢起她自己的被子,藏在屋里炕上的缸里(急糊涂了)。等我刚上炕,土匪就进屋了,母亲根本来不及再藏别的东西。土匪走后,她坐在炕边上,母亲愁得只知道哭,一看炕上只剩下我们姐弟和母亲的破被子,破框子里空空的,什么也没了。
在五字湾被抢过两次后,母亲的身体大不如前,她经常犯癫痫病。为了安慰母亲,怕再被土匪抢,父亲决定去个比较安全地方住。全家搬到了叫马场壕的小村。雇了一辆牛车赶了两天,到了目的地,在半路上住了一晚上。接纳我们的是一家刚失去12岁男孩儿的穷苦人家,当那家母亲看见我们姐弟俩,就想起了她的孩子。听那母亲说,前几天,他们大人出较远的地方干农活儿,把男孩留在家里看家,孩子在门框坐着,手里抱着一个小盆儿掰豆角,突然跑过两只饿狼,叼住男孩儿,拖向房后空地上撕咬,血流的到处都是,等大人回来一看, 只见房后只剩下一条腿了......这位母亲哭得像个泪人似的。这种情景让我终生难忘,在那个苦难的年代里,天灾人祸,使人实在难以度日。那时我六岁。
第二天到了马场壕,租了一间放杂物的小南房子,房东有个男孩儿叫偏头,后来成了我和弟弟的玩伴。父亲还干老本行-货郎,换点米面,维持生活。我们姐弟俩有一天去与扁头去挖野菜,到了山坡上看见坡上长着好多苦菜,我抓住一根长长的苦菜,用力向外拉,根很长,突然根断了,把我也摔倒了,顺着土坡向下滚,掉在坡下的一个大水坑里,水不深,是个饮牛水坑,坑下是条干河,我自己爬上来,全身湿透了。回到家后,挨了母亲一顿骂,不让我们再去那危险的地方。把湿衣服脱下,光着身子站在院子里,不敢回家,只听妈妈骂声,心里很委屈。
不知过了几个月,半夜里听见远处传来枪声,不一会儿,家里闯进一个生人,喊着让把灯点着,我母亲点着小油灯,弟弟睡着,我也被吓得躲在母亲的身后,只见那人翻箱子,把几件衣服拿走,又把父亲刚送回来的估计十来斤莜面也拿走。那人走后,母亲吹灭油灯,坐着不敢睡,只听见远处还想着密集的枪声,不知什么人在打仗。
躲到这个地方防土匪,没想到又遭一次匪劫,几年遭三次土匪,家里一贫如洗。日子过得像鸡一样,刨一爪子吃一口,实在难以维持。这时,母亲又怀孕了,只得再回到五字湾。家里过着穷苦日子,母亲的癫痫病老范,一犯病就口吐白沫躺在地下,眼睛瞪着,四肢抽搐...... 父亲老不在家,我们又小不知所错,只知傻看着母亲慢慢醒来。有一次,母亲犯病时,她正在做饭,不一会儿,她把水瓢放在锅里,向炕边一靠,人慢慢向下滑,滑到灶台与炕的角落底下...... 我在炕上直喊妈,约半小时左右,她从地下站起来,再开始继续做饭,那天父亲不在家。后来有一次,母亲犯病,竟从炕上摔在地下,她流产了,在我的记忆中,地下有血,还有些流产物。可怜的母亲一次次让病魔折磨的浑身是病,没钱治病。
1950年5月,生下一个男婴,我的小弟弟。这年她的身体非常虚弱,成天坐在炕上,不能下地,屁股上生起座疮。邻居来串门时,她老问人家这句话:你看我死了死不了?人家老说:死不了。这年腊月,母亲再也受不了身体上的病痛,含着泪离开了八个月的小弟弟,和六虚岁的大弟弟,八虚岁的我。妈妈才36岁,父亲38岁。以后,父亲怕我们受委屈,再也没找女人。
母亲去世后,把父亲愁坏了,小弟弟没奶吃,本家的叔叔抱着小弟弟去乡里打问奶妈,由于小弟弟体弱,谁也不敢收留,生怕喂不成人。最后,在五字湾河对面的山里终于找了一家姓马的奶妈,直至弟弟八岁才从马家接回来念书。
1950年秋,老家的二叔来内蒙准旗看望我们,正遇上妈妈病重。二叔在准旗住了几个月,顺便与一同来的乡亲们买了些马匹和皮毛,在51年春暖后,组成马帮一样的十几个人的队伍回老家,顺便把我和大弟弟一起带回老家。通过山西走了不知多少天回到老家,听大人说走了半个月时间,路上过黄河,翻大山。让我步走一会儿路,骑一会儿马,我九虚岁,走不动,坐在地上哭。二叔只让大弟一直坐在马鞍上,就让我走一会儿路才能骑一会儿,是为了让马有缓气的时间,那时我哪里懂得心疼马匹只想骑。马鞍前面用粗柳条做了一个弓型,让我们握住(怕从马上掉下来特别作的)。有一天过河,让我俩骑马过河前,大人们一再叮嘱,手握紧弓,眼向前看。大人们找了个水浅的地方过河,一个头人骑马带头过河,到了河中间,我和弟弟不时看着河水,身子渐渐斜向一边。在远处的二叔和其他大人看见了大声喊:秀妮!起房!抬头向前看! 如果不是大人们及时看见,我们俩就会掉下河里,太危险了。
回到老家,我和弟弟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妈妈离开老家时曾发誓:再也不回这鬼地方了。二叔把我们带回去,我那后奶奶不肯接收,二叔与她不知谈了多少次,承诺明年给她300元大洋,她才答应只收一个,于是弟弟就去了后奶奶家,我留在二叔家。二叔的家在一个四合院内,占北面几间房和南面的几间房。西屋是二层楼,和南屋的几间房,当时是小学的教室。据说是斗地主时,把地主的一套院分给了学校和我父亲与二叔,后来我父亲的屋全送给了二叔。北面大屋里有一盘大炕,对面有个小炕,小炕北边是放粮食和杂物的,我就睡在大炕上。
当时二叔只有一个大女儿,名叫丑女,二婶怀着大肚子,二叔二婶和丑女住在小炕上。老家的煤很难烧,全是煤面儿,要和上粘土,架在直筒型的土炉中,中间儿用火柱捅个眼儿,慢慢儿才能着起来,从眼内冒出火苗,用这微弱的火苗做饭,不做饭时,上面盖块铁盖,冬天也是这样取暖。如果天暖后,做饭要在南屋的像缸一样的小粗灶上烧麦秆和麦皮等,还要一边拉着风箱一边加柴,家里的大小灶都没有烟洞,烧的无烟煤,暖气顺着灶洞循环,虽说无烟,可是家里的墙像黑漆刷过一样乌黑。我睡下后有时被冻醒,晚上不敢起来解手,再次睡着后就梦到找厕所,第二天醒来一看尿在破皮袄上了(皮袄是母亲的,带回老家了),也不敢说就捂在原地,到晚上照旧睡在潮湿的被窝里。这样经常尿炕,时间长了,把炕板石都湿塌下去了二叔才看见,给我换个地方睡。因为这事,二婶就和二叔吵起来,二婶说:你找我时,说你是老大,现在又出来个老大,还把这个害给我带回来,我不管了,你们叔侄一起过吧,于是二婶气得回了她娘家。她回家的几天里,二叔把我搬到小炕上和他一起睡,真暖和。那几天,二叔给我偷吃花生等干果,真香。二叔常与村里的乡亲们出外给人家驮脚送货,有时也买点干果,一拿回来就被二婶儿藏起来,一点也不给我吃,她把花生挂在屋梁上。等她不在时,有时我搬个凳子偷拿一把吃,如果让二婶儿看出来就是一顿打。
二婶儿生下小弟弟-海为。在月子里常让我给洗尿布,刷掉粪便后再用凉水洗,把我的手冻得骨头疼。有时泡尿布的水上冻了一层冰,照样让我洗,在院里的葡萄架下石板上搓洗,手冻的没有知觉,那时我才九虚岁。二婶的母亲和妹妹就在本村聂门街上住着,二叔外出时,老太太过来照顾二婶,给我和丑女做饭。
秋天收完秋后,二叔把没开花的棉花桃子晒在屋顶上,等它裂开口时,人工把棉花扒出来,称次棉,留着自己用。扒棉桃就成了我的活儿,深秋时节,整天坐在屋顶上扒棉桃。有一天,丑女上来玩,那时他五岁,玩儿着玩儿着说要拉屎,让她下去,她不肯。我看见邻居屋顶上有个破盆,于是我让丑女拉在破盆儿里,准备一会儿我给倒在南院屋外的马圈里,我在专心扒棉桃,就把倒粪的事忘了。等第二天上午,邻居来找二审,丑女不认账,硬说是我拉的,我给二婶说了过程,她不信,拉住我的手就是一顿毒打。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晚上睡觉做噩梦,半夜哭个不停。二叔把我拉在大门外,我还哭,回来还哭,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连几天都哭,吵的大人没法儿睡觉。
在二叔家住了一年左右时间。10岁那年夏天,父亲回来看我们,带回300元钱给后奶奶,让我们两秋天上学,又去求后奶奶连我一起收下。在众乡亲劝说下,后奶奶勉强收留下我,与大弟弟可以常在一起了。
去了后奶家里也没什么好日子过,每天晚上让我给姑姑绕线,姑姑织土布,自己纺得线,要绕成团儿......小孩儿爱打盹儿,到深夜才让睡觉, 第二天早起不来。上学时每天迟到,老师和同学给我起了个外号:甄迟到。我没上过一年级,直接跟了二年级,所以写字的基础没打好写的很难看。
记得在准旗在父母身边时上过一段私塾,稍有认字基础。那一段的记忆很模糊,光记得有一位男同学,不知犯了什么错,老师让他罚站,还用木板打手。同学们上厕所不能一起去,要一个个轮着去,去时把墙上的木牌挂在胸前,回来再把木牌挂在墙上,下一位同学再去。所有的学生都坐在炕上的小桌子后,几个年级的在一个教室里。
去后奶家后,大弟弟跟我说后奶奶虐待他的事: 后奶家里喂着一头很大的骡子,需喂青草,天天叫七虚岁的弟弟出地里割草。有一天弟弟去割草,因草少没割多少,回到村口时,有一个好心的本家青年人给弟弟出了个主意,用木棍儿把草撑起来回去交差,看上去满满一箩头。回到家后,后奶奶见了高兴的夸说:今天没少割,随手压一下草闪空了,这下可是犯了天大的罪了,后奶抬手就打,弟弟转头就跑,一口气跑在别的bulong里。后奶奶的小脚哪能追上他,弟弟看见一个新修的厕所,进去后,纵身跳在新茅坑里,不敢出来。到天很晚了,后奶奶有点着急了,她叫了几个邻居,打着灯笼满村子找。边走边叫弟弟名字,说:你回来吧,我不打你...... 弟弟也又饿又累,后来自己爬出茅坑,慢慢儿走回家。后奶奶也没敢再说什么,这件事过去了。
等我去后奶奶家,每早起来还得倒尿盆。有一次,我到尿盆时抓不紧,连盆一起摔出去了,盆破了,我也没敢说,就去上学了。等中午回来,后奶奶对我一顿打骂,一手拿笤帚,一手拉住我,一边打一边骂。她心太狠毒,光向头上打,打的满头大包,还不解恨,用指甲掐我的小臂肘横纹处,掐的胳膊肘上直流血,她见了才罢手。至今右肘右侧还留着拇指掐的疤痕。
现在想起这次毒打我不由得哭了一顿(每次看到这里我忍不住痛哭流泪-----儿子注)。同时,回想起二叔给我讲后奶奶虐待他父母的事。二叔是在他八十大寿时,我们姐弟三人回老家给二叔祝寿时给我们讲的。后奶奶是二叔的亲妈, 如果不是后奶奶太恶毒,二叔这亲儿子也看不惯,也不会给我们讲。二叔跟我说:你妈在家时,你奶奶吃饭吃不给你妈吃好窝头,只让她吃菜糠窝头。一次你妈等开锅时,去锅里抓两个玉米窝头就往西屋走,给孩子吃,气得后奶奶骂个不停。当时父亲和爷爷去内蒙,母亲身边还有两个子女,不吃点有营养的也不行。二叔还说,有一次家里吃‘和菜面’。后奶奶只给我父亲盛了一碗净面条叫父亲吃,父亲也觉得奇怪,父亲不肯自己独自享用,就接过面碗要往锅里倒,后奶奶夺过面碗放到地下的角落里。二叔说:这碗里有毒,她想毒死父亲,报复母亲。有时二叔也看不惯后奶奶的所作所为,也会出面保护父母,与后奶奶理论几句。
我们姐弟在后奶家住了两年多,我俩前后出麻疹,一点特殊待遇也没有过。正当放假天天去地里干活儿割草,在家里也不闲着,坐在院里搓麻绳子,供大人纳鞋底。由于加上营养不良,后来就手脚粗糙、裂口。
我们回到老家后,与弟弟去太井看姥姥。老人家对我们真是亲热,问长问短。当问到母亲时,我和弟弟都说:我妈明年回来呀,姥姥开始信以为真,非常期待母亲回到她身边。当外人问我时,我就实话实说:我妈妈死了。当姥姥从外人那里听说母亲死了,回来问我时,我就说给她:我爹让我撒谎对你说妈妈明年回来,是怕你着急伤心。姥姥知道母亲死了,就天天坐在谷场边哭,眼红了,点些眼药。
我们从姥姥家返回二婶家时,姥姥给我带了一块新布,让二婶给我过年做新衣裳,这块新布我一直没穿上新衣,到了过年时只用暗红色破棉布,给我做了件单上衣,还补着补丁。姥姥还给弟弟带了一块布,也没见给弟弟穿上新衣。在姥姥家最好吃的就是泡泼好得柿子,真甜脆。
有一次夏天上房顶上睡觉前,被蝎子蜇了手,疼的我哭个不停,姥姥心疼的哄我,给我在蜇伤处抹了不知什么药,回房里睡在被窝里,姥姥拍着我睡觉,这种亲情使我终生难忘,这与后奶奶对我们的虐待真是天壤之别。在后奶奶那里我也被蝎子蜇过两次,我一声没哭过,忍着疼自己揉搓。后奶奶根本不知,知道了也不心疼。
在老家,我记得还去过老姨家住过几天。老姨是姥姥的妹妹,住在龙化村,老家夏天都有在房顶上睡觉的习惯。去老姨家第二天睡在屋里单人床上,可能是走累了,就给老姨的新毡上尿了一片,真是不好意思。第二天在房顶上睡,很凉快,还听见远处水塘里的青蛙呱呱的叫个不停,听着很好听,不一会儿就入睡了,睡得很香。
△有一次割麦子,左手抓住一把麦秆,右手用镰刀割,镰刀一下滑在左手食指上,一看指甲盖上的肉张开一个小嘴一样的裂口,鲜血直流,没敢给大人说,自己用手捂住伤口的两侧。后来还有一次割草,又在同样的伤口割了一刀,至今还留着疤。
△据说土匪抢东西时,忙着见东西就拿,有时包裹里包的什么也不看,回去在山上才打开查看包裹,有用的就留下,没用的就扔到山沟里。我妈妈的小脚鞋,和裹脚布,他们肯定不要扔掉了,害得我母亲没鞋换,只得在动手做鞋。
△有一回,父亲收的毛,卖给一家织地毯的手艺人,他们没钱付,多次要钱都没结果。父亲想了一招,把我们姐弟俩领上去要钱(那时母亲病重)。那家人只好答应给两块小尺寸地毯(二尺宽,四尺长)。要回地毯后,怕被土匪抢走,就连夜在地下挖了个藏东西的小地窖(炕边下角处),把两块地毯藏进去才没被抢走。等二叔带我们回老家时,给了二叔一块,自己留着一块。等父亲去世后,大弟弟把它卖了破烂(虫咬了不能用了)。
在老家去姥姥家,经常与后姥爷的孙女一起干活,有时她想妈妈,带着我去她妈妈的墓地里,哭诉她继母怎样对她不好,我也跟着哭一场,我也想妈妈(我也想妈妈-----儿子注)。
(我在19**年回老家,给二叔过八十大寿时,和我后爷爷的孙女我的姐姐见了面,并留了影)
在老家去姥姥家时,经常与后姥爷去山上放牛,有十几头牛,都是村里各家的耕牛,等冬天赶出去吃山上的干草。每天姥爷口喊:“撒牛了”, 有牛的人家就把牛放出来,姥爷赶着他们上山,我也跟着赶牛。上山后,牛悠闲地吃着草,姥爷坐下抽烟,用火镰打火点烟,火镰样子很轻,两块铁用力一打就有火花,把一块草纸点着了小火,用这小火可点焊烟抽。秋天,有时跟着后姥爷去自家地边的柿子树上摘柿子,回来给我发泡,放在热锅台上倒上水,几天后就能吃了,好吃,又脆又甜。
在老家二叔那里时,经常让我牵着马去地头地边,让马吃青草。有一次,正放着马,天突然下起倾盆大雨,我拉马往回走,马不走,因是顶头风。那是我十一虚岁,哪里有劲拉得动马,只听见二叔喊我回家,二叔是在房顶正遇顺风,喊话听的很清楚,可我答应他听不见。等雨停后,二叔来找我,我也正好往回走。回家后,晚上我发烧,眼睛又红又疼,二婶儿的老母给我治眼病,用两手用劲按住太阳穴向后绷,使眼去火,又点眼药,不几天病好了,又继续放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