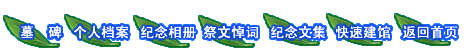妈,盛花从这个周开始正式上班了,周末佳佳姥姥过来了,这几天在这里照顾佳佳,他舅舅还怕佳佳不跟姥姥,老打电话问怎么样。妈,佳佳很乖,也不闹,有她姥姥在这,爸也轻快不少。妈,如果您在佳佳会更幸福的。
妈,一百六十八天了,儿子一想起您离开儿子了,就觉得非常的孤单无助。这几天正宇姥姥在这照顾佳佳,做饭,从正宇身上总是能看出来,和您在这不一样的感觉,也说不上来什么,和您相比,应该是和他姥姥多了些客气,少了些亲昵。妈,您宝贝孙子孙女没有奶奶了,也是很可怜的。
妈,咱娘俩一起继续看书吧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第九章
不要小看它,它的力气其实很大。单是把它装进纸盒,再把纸盒用绳子捆上就费了我不少力气。
一路上它更是鬼哭狼嚎。
我一手扶着自行车的车把,一手背过去不断拍打着夹在自行车后座上的纸盒,口中还不断喊着“咪咪、咪咪”地安抚它。
它在纸盒里乱蹬乱喘,弄得自行车摇摇晃晃很不好骑,又赶上修路,不时还得绕行或下得车来推行。到了先生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在十月下旬的天气,我竟能汗流如雨。
把它一放进客厅,我注意到妈没让人扶,一下就坐起来了。
我马上想,妈真是躺下就不会坐起来吗?
我也看见妈欣喜的笑了。妈,我为的不就是您这短短的一笑吗?可是我突然发现,我的背包忘在门户不严、等于是废屋的老家里了。那里面有我全部的钱财细软,只好返回去取。等再回到先生家里,已是午夜十二点多。我一头扎在床上,一下就睡着了。
不过睡了几十分钟,又突然醒了。然后就睡不安稳了。虽然有小阿姨陪妈睡在客厅里,我还是不断起身到客厅里看望她,见她安详地睡着,便有了很实在的安慰。
当然,大功告成的兴奋也使我无法入睡,我长久地注视着她,就像欣赏自己的一个的杰作。我怎能知道,那其实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而妈就要离我而去?
十月二十二号,星期二。
很早起身,说是给大家做早饭,其实真是为妈。
煎蛋和“培根”。国产的“培根”质量不太好,只能拣最好的几块给妈,余下的是先生和我、小阿姨平分秋色。
妈的手又不大好使了。一块煎得很好的“培根”从她筷子里掉下来,妈像犯了过错,轻轻地“哎呀”了一声。
我说:“没事。”
她懊恼的也许是那块煎的不错的“培根”,更懊恼的也许是我为她的劳作让她白白地掉在了地下。
这是很小的一件事,可我现在仍然能清楚地记起,我想它肯定不是无缘无故在我心里留下了痕迹。
对,我懊丧那么好的一块“培根”妈没有吃到嘴里去。一块煎得很好的“培根”
就那么容易得到?要以为那仅仅是一块煎得很好的“培根”就错了。
还有,妈那像是犯了过错的神态让我为之心痛。妈,您就是把什么都毁了,谁也不能说个什么。这个家能有今天,难道不是您的功劳?
后来妈要上厕所,我有意要她锻炼自己从马桶上站起,没有去扶她,也不让小阿姨去扶。
她先是抓马桶旁的放物架,企图靠着臂力把自己拉起来。我把放物架拿开了,迫使她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可她就是不肯自己站起来。
我那时真是钻了牛犄角,认为站得起来、站不起,对她脑萎缩的病情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从这样小的事情上就倒退下去,以后的倒退就更快了。
为了让她自己站起来,实在用尽了心机。
我先是假装要把她抱起来,然后又装作力不胜任、歪歪扭扭像要摔倒的样子,嘴里还发出一惊一乍的惊叫,心想,妈那么爱我、疼我,见我摔倒还不着急?这一急说不定就站起来了。
可是不行。
我又推高发动的档次,打出唐棣这张王牌:“唐棣年底就回来了,她不是说要带您去吃遍北京的好馆子吗,您自己要是站不起来,她怎么带您出去呢?”
还是没用。
深知她盼望着一九九二年我带到她美国去和唐棣团聚,又说:您也知道,飞机上的厕所很小,根本进不去两个人。您又爱上厕所,要是您自己站不起来,我又进不去怎么办呢?
这样说也没用。又知道妈极爱脸面,在先生面前更是十分拘谨。便故意打开厕所的门,明知先生不过在卧室呆着,却做出他就在厕所外面的样子,说:“你看,妈就是不肯站起来。”
妈着急地说:“把门关上,把门关上。”
就是这样,她还是站不起来。
后来我发现,她起立时脚后跟不着地,全身重量只靠脚尖支撑,腿上肌肉根本不做伸屈之举。既然不做伸屈之举,自然就不能出劲,不能出劲怎么能自己站起?
我立刻蹲在地上,把她的脚后跟按在地上,又用自己的两只脚顶住她的两个脚尖,免得她的脚尖向前滑动。以为这就可以让她脚掌着地。但她还是全身前倾,把全身重量放在脚尖上。而且我一松手,她的脚后跟又抬起来了,这样反覆多次,靠她自己始终站不起来。
现在回想,这可能又是我的错。
她术后第一次坐马桶的时候,突然气急败坏地喊道:“快,快,我不行了。”
我吓得以为出了什么事,奔进厕所一看,原来她上身前倾。两脚悬空,自然有一种要摔向前去的不安全感,难怪她要恐怖地呼叫。
那时我要是善于引导,将她整个身体前移,使她两脚着地,并告诉她坐的时候重心应该稍稍往后,起身时重心应该前移,以后的问题可能都不会有了。
我却不体谅她大病初了,在正常生活前必需有个恢复过程,反而觉得她的小题大作让人受惊,根本不研究她为什么害怕,就气哼哼、矫枉过正地把她的身体往后一挪。她倒是稳稳地坐在马桶上了,可是两只脚离地面更远了,如果不懂得起身时重心应该前移,使两个脚掌着地,再想从马桶上站起来就更不容易了。
对于一个本来就脑萎缩、又经过脑手术的老人来说,手术后的一切活动等于从头学起,第一次接受的是什么、就永远认定那个办法了。以后,没有我的帮助,她自己再也不能从马桶上站起来了。
人生实在脆弱,不知何时何地何等的小事,就会酿成无可估量的大错。
也许她的敏感、她对这个手术的一知半解也害了她。自己给自己设置了很多受了伤害的暗示。她认为既然是脑手术,自然会影响大脑的功能。
大脑的功能既然受到伤害,手脚自然应该不灵。
这时她又叫小阿姨扶她起来,我因为急着到装修公司去,就嘱咐小阿姨别扶妈,还是让妈自己站起来。
在装修公司忙了一天,回家时一进胡同,恰好看见妈和小阿姨从农贸市场回来。
小阿姨没有搀扶她,而是离她几步远地跟在身后。她连手杖也没拿,自己稳稳当当地走着。这时她看见了我,就在大门口停下,等我走近。
我搀扶着她走上台阶,她的脚在台阶上磕绊了一下,我想,好险,幸好我扶着她,就回头对小阿姨说:“走路的时候你可以不扶她,但要紧跟在她的身边,万一她走不稳,你得保证一伸手就能抓住她。上台阶的时候可得用劲搀扶着她,不然会出事的。”
妈还买了半斤五香花生米,这就是妈这辈子最后一次上街、最后一次买东西了。
不过半斤五香花生米。晚上我问小阿姨,妈是不是自己站起来的。我是多么想要听到这样的消息,那会比什么都让我高兴。
小阿姨说不是。还是她扶妈起来的。
我感到无奈而又失望。
她说,妈还对她说:“你干嘛不帮助我?我请你来就是要你帮助我的,你怎么不听我的净听你阿姨的呢?你别听你阿姨的。”
妈不但过于敏感,且取向颇为极端。
她之所以这样讲,一定是又为自己制造了一份寄人篱下的苦情。诸如,因为她是靠我生活,自然在这个家里说话不算数;自然指挥不动小阿姨:保姆自然势力、谁给她工资她就听谁的……等等。
妈是永远不会理解我的苦心了。她不理解我的苦心倒没什么,让我不忍的是她会从自己制造的这份苦情里,受到莫须有的折磨。
晚上,大家都睡下以后,我还是不断到客厅里去看她。她似睡非睡地躺着,猫咪亲呢地偎依在她的怀里。它把头枕在妈的肩头,鼻子拧在妈的左颊下面。我在沙发前蹲下,也把头靠在妈的脸颊上,静静地呆了一会儿。妈没有说话,一直半合着眼睛。
那就是我们少有的天伦之乐。我当时想,妈的病好了,我们还能这样幸福地生活几年。
为了不影响她的休息,我呆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十月二十三,星期三。
一早我就起床了,把头天晚上泡过的黄豆放在“菲利普”食物打磨机里粉碎,给妈磨豆浆喝。此物早已买来多时,这是第一次使用。
然后我又让小阿姨去买油饼。
妈吃的不多。她的食欲反倒没有在医院时好了。
服侍妈上厕所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臀部有一圈出血性紫癍,根据部位推测,显然是昨天我让她练习自己从马桶上起立未成,在马桶上久坐而致。
当时我倒是想了一想,即便坐的时间长了一点,怎么就能坐出如此严重的一圈瘀血呢?但我很快就否定了可能有问题的取向,心里想的总是妈手术后百病全无。
要是我能往坏处想一想,肯定早就会发现问题的严重。
也因为我们家的人,身上常常出莫明的出血性紫癍,过几天就会自行消失。妈也如此。我也就大意了。
但这一次发展到后来,轻轻一碰就是一片。所以星期三的发现,已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从这一圈紫癍的发现到妈过世,不过就是五天时间。
如果说妈去世前有什么征兆,这就是最明显的征兆了。
回忆妈这一场劫难的前前后后,我甚至比医护人员还能及时发现妈各种不正常的体症,只是我既没有医学常识,不了解这些不正常体症的严重后果,又没有及时的求救于医生,就是求救于医生,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采取应有的措施,我更没有坚持将这些不正常体症的来龙去脉弄个一清二楚。妈是白白地生养我了,她苦打苦熬地把我拉扯大,哪想到她的命恰恰是误在我的手里。我蹲在马桶一旁,等着帮妈从马桶上站起。这时,妈伸出手来,一下、一下,缓缓地抚摸着我的头顶,突然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我立刻感到那声音里颤绕着非常陌生的一种情韵。丢失了我几十年里听惯的、她也讲了一辈子的那个声韵。心里涌起一阵模糊的忧伤。
现在才悟到,那声音里弥漫着从未有过的无奈和苍凉,以及欲言还休的惜别和伤感。
那是一句没有说完的话,现在我的耳朵里已能清楚地回响起深藏在那句话后面的万千心绪,和没有说出的一半:“……可是我不行了。”
她也许曾经想要把后面的一半说完,可她还是不说了,咽回去了。
她的手虽然一下、一下抚摸着我的头顶,却又轻得似乎没有挨着我的头发。
虽然没有挨着我的头发,我却能感到自她心里尽流着的、而又流不尽的爱,绵软而又厚重地覆盖着我。
那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像是重又回到她襁褓中的婴儿,安适地躺在她的怀里。
虽然她老了,再也抱不动我,甚至搂不住这么大的一个我了。可是,只要,不论我遇到什么危难,她仍然会用她肌肉已经干瘪的双臂,把我搂进她的怀里。
虽然她的左肩已经歪斜得让她难以稳定的站立,她还会用她老迈的身躯为我抵挡一切,那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肯为我这样做的。
我一生爱恋不少,也曾被男人相拥于怀,可我从不曾有过如母亲爱抚时的感动……也不曾有如母亲的爱抚,即使一个日子连着一个日子也不会觉得多余……
从她手掌里流出的爱,我知道她已原谅了我。不论我怎样让她伤心;怎样让她跟着我受穷多年;怎样让她跟着我吃尽各种挂落……她都原谅了。
可是上帝不肯原谅我,为了惩罚我,他还是把妈带走了。
就在那一天,我对先生说,我要给妈找一个心理医生,来解决她的思想障碍问题。我觉得她手术后躺着坐不起,坐着站不起是思想障碍的问题。
但那时最要紧的是忙着找关系,以便请到最好的医生为她做放疗,心理医生的事还没来得及落实,她就走了。如果这个问题早解决一些,妈的体力一定不会消耗那么大,这又是我的过错。
下午,妈和小阿姨一起包了饺子。小阿姨告诉我,妈还擀了几个饺子皮。后来妈就说累了。我不知道我是否吃到妈包的那几个饺子,或哪一个饺子,反正这是妈这辈子给我包的最后一次饺子了。
晚上妈对我说:“沙发太窄,猫也要跳上来睡,把我挤得不得了。特别是昨天,你们两个人还都在我脸上蹭来蹭去的。”
我才知道昨天晚上我和猫偎依在她身旁的时候,她其实没有睡着。她之所以闭着眼睛,不过是在专心致志地享受我们对她的依恋。
她又说:“前天晚上把它刚接回来的时候,它对这个新环境还有些认生,对我也有点生疏,昨天就好了。拼命的往我怀里钻,简直像要钻进我的肉里。”妈微微地笑着。这真是妈值得炫耀的感受,连一只牲畜都能分出好歹,那是怎样的好歹?
所以它来只钻妈的被窝、只让妈抱。当时我就让妈睡到折叠床上,让小阿姨睡到沙发上去。
妈坐下就站不起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我很发愁,不知怎么才好。
临睡以前,我忍不住拿出她的核磁共振片子,万不得已地吓唬她说:“本来我不想告诉您,但是现在不告诉您也不行了。您瞧,您的脑子已经萎缩的相当厉害了。
医生说,您自己再不好好锻炼。再不好好恢复各方面的能力,脑子还会继续萎缩下去。脑子一没,人就活不成了。照这样下去,再有三个月就要死了。但医生说,只要您好好锻炼,好好恢复您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脑子还会再长大,那就不会死了。“
想出最后这一招,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妈是不会放心把我一个人丢在世上的,为了这个,她也得拼上一拼。
妈平静地躺在折叠床上,眼睛虚虚地看着空中,什么也没有说。
这当然又是我的大错。
从以后的情况来看,这一招,不但没有把她激发起来,肯定还给她造成了很大的精神负担。她精神越紧张,各方面的功能就恢复的越不好。
对妈有时可以用激将法,有时不能。火候掌握不好就会坏事。
我猜想,她后来对胡容说:“我要走了,我活不了几天了,我累了。”肯定和我这样吓唬她有关。我把她吓着了。
十月二十四号,星期四。
下午带妈上北京医院联系放疗的事。
我拿了甲大夫的介绍信去找关系,可是甲大夫介绍的那个关系不在,只好挂了一个普通的门诊号。
我们先在候诊室等着叫号。为了抓住每一个帮妈锻炼脑力的机会,我装做忘记了我们的号数,问她:“妈,咱们是多少号?是不是该叫咱们了?”
妈说:“三十七号。”
我说:“瞧,您比我还行,我都忘记咱们是多少号了。”
护士叫到三十七号的时候,妈已经拉着前排的椅子背自己站起来走了过去。我想她一定在注意听护士的叫号,否则怎么会在她走过去的时候护士正好叫到她呢?
尤其是在乱糟糟的人群里,护士的声音又不大,连我听起来都很吃力。而且她自己站起来的时候很利索,这又让我感到信心倍增。
我们等叫号的期间,先生又去找了他的关系户。很凑巧,先生的那个关系户在,我们希望得到她的治疗的放射科主任也在。
我对妈说:“妈,瞧您运气多好,要找的人都在。”
我可能变得极其琐碎、极其牵强附会,不论可供回旋的地盘多么小,我都想在上面挖出点让妈振奋的东西。
放射科主任给妈做了放疗前的检查。
她让妈用食指先点手心、再点鼻尖。左手点完右手再点,而且要求妈越点越快。
妈做得很好。
主任说:“老太太真不错,这么大年纪,做这么大手术后果还很好。”我听了这话比什么都高兴,这不是又一次得到证明,妈很棒。何况还是一位主任医生的证明。
主任约定我们下星期一,也就是十月二十八号来医院放疗,同时交付所需费用和办理放疗的一应手续。然后,她让我拿着妈的病理切片到病理室去做结论,以便作为放疗的依据。
我们乘电梯下楼的时候,电梯里人很多,我用双手护住妈,挡住那些拥挤的人说:“别挤、别挤,这里有个刚动完手术的老人。”
电梯里的人见妈那么大年纪还接受手术,都感到惊奇,也许还有一点敬佩。羡慕妈在这样的高龄还有这样硬朗的身体;一个老头还向我打听妈的年纪,一听妈都八十了更是赞叹不已。
我为有身体如此之好、生命力如此之强,能抗过如此大难的妈而自豪。好像她能顽强地活下去是我极大的光荣。
下楼以后我在挂号厅给妈找了一个座位坐下,然后到后院去找病理室。病理室很不好找,拐来拐去才找到。病理室的大夫看了妈的切片也说,妈的瘤子是良性的。
他给我开据了放疗需要的病理诊断,我们就回家了。
下门诊大楼的台阶时,我怕妈摔着,便站在她面前,和她脸对脸地倒着下台阶。
万一她一脚踩空,我还可以抱住她。
这时我又忧心起来,我发现她的脚分不出高低了。她果然一脚踩空在我的脚上,并且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样子。但是她脚却很有劲,像她术后第一次下地踩在我脚上一样,很痛。要不是我挡着她,非从台阶上摔下来不可。我也立刻想到昨天她从农贸市场回家的时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磕绊的那一下。
我烦闷地想,就在手术前妈的脚还能分出高低的啊。
回家的路上,不知怎么说起她穿的运动衫裤,妈还略微诙谐地说:“美国老太太。”
她在美国生活期间,见惯了美国人的日常穿着,多以舒服、方便为原则。我认为这个办法不错,特别在妈日渐老迈、手脚也不太灵便以后,运动裤上的松紧带,要比西裤上的皮带简便多了。另外她的脚趾因生拐骨摞在一起,一般的鞋穿起来挤得脚疼,穿宽松的运动鞋就好多了,所以后来就让妈改穿运动衫裤、运动鞋。
车到和平里南口,快过护城河桥的时候,妈说:“到了。”
我说:“嘿,妈真行,才走一遍就认出来了。”可不是嘛,走一遍就能从北京千篇一律的街道中认出某一条路口,不很容易。
到家以后妈满意他说:“大夫挺负责任,检查的很认真。”说这话的时候,离妈去世还有三天半时间,而妈的脑子还不糊涂。
妈满意我就满意了。
这就是妈这辈子最后一次上医院了。
这天晚上妈又发生了“谵妄”。自己下了地,蹲在地上小解后,又自己站起来回到床上睡去了。
第二天小阿姨问她:“你能蹲下?”
妈说:“你不扶我,我不蹲下还不尿在裤子上。尿在裤子上你阿姨还不说我。”
她这样说的时候,好像不存在她近二十年不能下蹲的事实。但她似乎也分不清白天和夜晚、过去和现在的事了。
我知道这件事后很高兴,当做可喜的事情对先生说,后来又对胡容说。因为她近二十年不能下蹲了。可是在梦中,她不但蹲下、还自己站了起来。这是否说明她白天的表现,并非是各部器官的功能丧失?
我也更相信妈最后能站起来。可是我也更不能容忍妈自己不能站起来的表现了。
妈对我把这件事说给先生很不高兴。说:“多不好意思。”
后来又对胡容埋怨,“张洁干嘛要对老孙说这件事,多不好意思。”
胡容说,“张洁是高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