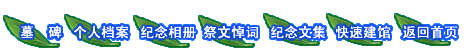爸要回家
一
很多年以前三月的第二个早晨,太阳刚刚出来,天上就出现了红彤彤的一大片云彩,就在这时,笼罩在红光中的一栋房子里传出了一个初生婴儿响亮的啼哭,仿佛是在向全世界大声宣告:我来了!
当然,这些明显有点夸张的传奇,都是多年以后我爸告诉我的,他还说那个时候他高兴极了,当场就决定为我取名为“红”,小名“红娃子”。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WG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因为家庭出身不太好,爷爷和我爸都遭受了或大或小的冲击,我的到来一扫全家的阴霾,尤其是我的爷爷和奶奶更是高兴,他们甚至提出让我随他们一起去生活,可是我爸坚决不同意,于是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在孩子的眼里,爸爸常常是无所不能的,是随时可以拯救他们于水火的大英雄,是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后崇拜的第一个偶像。
那时的我们住在一个小县城里,夏天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一到晚上大家都会聚在院子里乘凉,每当这时孩子们就会缠着爸讲故事,他也不推辞,刚开始是讲书上的故事,等到实在没有新故事可讲的时候他还会临时编故事,兴致高的时候他也会讲自己的故事,他的厉害之处就是无论讲什么都能让人听得如痴如醉意犹未尽,一天讲不完就第二天接着再讲,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从那些故事里,我知道他是一九五八年从省城武汉来到这个小县城的,那时他只有二十四岁,这个时间我永远也忘不了,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不仅这个时间被反复提起,与之相关的事也被他津津乐道了许多次,比如一九五八年的前一年的十月十五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的那一天,他作为优秀青年的代表成为第一批乘车过大桥的人。更让我羡慕的是一九四九年五月的一天早上,还是中学生的他看见了满大街睡在路边的解放军,原来解放军是夜里到的,为了不扰民,就在路边合衣而卧了。那是他第一次听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这个名字,心中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他们学校的学生穿着统一的制服上街庆祝游行,衣服的扣子都是铜制的,闪闪发亮,引来别的学校的学生满心满脸的羡慕,实在是太拉风了!也是在那一天,他下定决心跟党走,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定要好好保卫新中国,建设新中国!
他生在武汉,长在武汉,全家人住在汉口三阳路一栋小洋楼里,他的父亲是当时省里不可多得的水利专家,母亲是汉口一家鞋厂的职工,家里还有两个弟弟,一家人其乐融融。他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会离开那个家。
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也是一个热血沸腾的年代,每个人都好象有使不完的劲,想为新生的共和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所以当省政府号召优秀青年支援山区教育时,当年还是省医药公司团支书的他马上就报了名,我奶奶当然舍不得他走,但他说过几年就回来,让她放心。
那个时候我爷爷刚好去了北京参加水利部的政治学习和业务培训不在武汉,那时通信也不象现在这样便捷,再说他怕爷爷不让他去,刻意隐瞒了这件事,于是当他到达那个小县城时,爷爷还不知道这个他寄予厚望的长子已经离开家一千多里了。
爸永远也忘不了,从武汉出发时,他们一行人都戴着大红花,当时的省委领导王任重书记亲自到码头送行。王书记和他们一一握手,勉励他们去最艰苦的地方为祖国做出新贡献,还说等过几年他们的任务完成以后,他会再把他们接回武汉。
就这样,一群朝气蓬勃豪情万丈的年轻人登上轮船,一路高歌一路欢笑,一直到宜昌下船时还是精神抖擞,热情洋溢不减分毫。
只是接下来的事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一群人分成几个小组分头再出发。他们以为会有汽车来接,可是没有,因为根本就没有公路。爸这一组有十几个人,只有个向导领着他们上路。
从小到大,爸只见过宽阔的平原,在他的印象中最高的山也就是龟山和蛇山了,和现在看见的山比起来,那两座山简直不能叫山,只能叫小土包了。踏上曲曲折折、上上下下的山间小路,走在路上,不敢向上看,因为总是看不到顶;也不敢向下看,因为一看就害怕,怕一不小心掉下去命就没有了。他们一起背着行李跟着向导走了一天也没有走到目的地,这下他们都有点慌了。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小村子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已经累得腰酸背痛的他们哪里还走得动啊,有的女青年开始哭了,可是没有办法还是要忍着疼往前走。爸没有哭,只是再也没有心情唱歌了,一路沉默。
天黑时还没有到,于是向导点起了火把,其他人就跟着他互相牵着手向前走。到晚上八点时终于到了那个小县城,可那里也是到处漆黑一片。后来才知道,这里供电时间短,而且停电是家常便饭,家家户户主要是靠点煤油灯照明,为了节省灯油,大部分人晚上都睡得很早。
向导带他们到县招待所住下来,不知道那天晚上还经历了什么,总之从那天开始,他想家了。
二
爸想回家,但是根本就回不去了。
形势变化很快,还没等他回去,武汉的家也搬到了贵州。这是因为爷爷的学习结束以后本来是想回武汉的,但是水利部的领导说湖北是水利基础相对较好的地方,而当时国家还有很多地方水利基础太薄弱了,急需专业人才去填补空白。于是,怀揣着科技报国的理想,当时已经人近半百的爷爷也响应国家号召拖家带口去了急需人才的贵州,先是在贵阳,后来又去了遵义,最后去了铜仁。
那些年,正是国家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无论在哪里,无论干什么,能活下来就是胜利了。
爸在县城的城关小学当上了小学老师,刚来时住在学校给青年教师准备的单身宿舍里,房间大约十平米,是和另一个人合住,除了放两张小床,余下的地方就不多了。两个人合用一个写字台,一个书架,一个脸盆架,衣服放在箱子里,箱子放在床下面。吃饭去食堂,没有自来水,好在一百多米外就有香溪河,那条河发源于上游的神农架,河水清澈,四季长流。爸很快就爱上了那条河,也很快学会了去河里洗衣服和用两个木桶挑水。
除了生活的不便,还有繁重的工作。学校老师不多,所以几乎每个人都是同时教几门课,几年下来,爸教过的课接近十门,当然他教得最多也最喜欢的还是语文和历史。
转眼间就到了一九六二年,那一年,爸的生活里有了我妈。年底的时候,他们结了婚。还是在那间小小的宿舍里,只是同住的人由同事变成了我妈。很快他们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可惜他因为去外地搞社教,长期不在家,女儿突然生病时他还在百里之外,等他好不容易赶回来,刚刚两岁的女儿已经夭折了,这成了他心里永远的痛。
后来小小的宿舍里又加上了我和一个弟弟,那张床变成了一个双人大床,四个人睡在一张床上,爸妈一头,我和弟弟睡另一头。那么小的房子是没有办法做饭的,所以吃饭还是去食堂,有时也去外婆家。
盼星星盼月亮,一个老师调走后,费尽周折,爸终于争取到了位于学校附近的三间平房。一间做厨房兼餐厅,另两间做卧室。不久后我妈生下了另一个弟弟,满心欢喜的爸请了一个木匠来家里,一下子做了两张大床,一个餐桌,一个写字台,一个碗柜,还有一个大衣柜,家里顿时气派了很多。虽说离河更远了,中间还有很长一段上坡路,挑水更难了,可是我们一点也不在乎,全家人都开心极了。
时光如梭,不知不觉中,我们在那个平房里住了十年。
爸已经人到中年了,他把对长女深深的遗憾和愧疚都转化成了对我们的爱甚至是宠溺,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给了我们无数美好的回忆。
无论多困难,他每年都要为我们三个过隆重的生日,带我们去照相馆拍照留念,并且一直坚持到我们满十八岁。
为了省钱,他带着我们三个去河边种菜,去山上打柴,去小煤矿买煤粉回来做煤饼。在自家的房前屋后盖上鸡舍和猪圈,只为了能省下买鸡蛋和猪肉的钱。拿笔的手一天天变得粗糙,可日子总算是安定下来了,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他很欣慰。
可他还是不安心,还是想回家。
家在哪里?
是武汉三阳路的那栋小洋楼吗?不,那里早就成了别人的家。
亲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于是只要存下一点钱,只要放寒假或是暑假,他就会带着我们全家去贵州爷爷奶奶的家。
每次回去,爷爷奶奶都很高兴。在那里,我们总会有漂亮的新衣服,有丰盛的饭菜,还有亲人之间说不完的话、道不尽的爱。如果说人间真的也有天堂,我想那里就是我们的天堂了。
可惜光阴似箭,我十四岁的那一年爷爷去世,又过了六年,奶奶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以后,爸很少说回家的事了,我以为,他现在是真的把小县城当成自己的家了。
三
其实,我觉得爸在县城的生活也是很幸福的。
首先,他在这里有了我妈。我妈年轻时可是公认的大美人,在我看来简直就和王昭君一样美。
县城的不远处就是昭君故里宝坪村,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十七岁以前生活的地方,那个村子里大部分都是姓王的人,传说就是她家的后代了。昭君故里的人世代以昭君为荣,昭君出塞的故事人人皆知。那里还有很多的景点,比如琵琶桥、珍珠潭、楠木井、梳妆台、昭君台等都与她有关。
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长大的女子,人美心善手巧。
我妈的家就在城关小学的后门附近,所以他们的相遇相爱几乎就是必然的。长大后的我们常常看着他们年轻时的照片,然后感叹我爸简直是赚得太多了,幸福啊!
爸的幸福还不止如此,虽说他一直在城关小学当老师,可是身边的同事也好,邻居也好,总是叫他博士或是教授。这样的称呼当然不是凭空来的。他经常穿着整洁的中山装,胸前的口袋里别着两支钢笔,一支红笔用来随时批改作业,一支蓝笔用来看书学习做笔记。所以他总是显得很有学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好象这世界上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每当我们有什么字不认识就去问他,因为他说自己就是活字典,而他也总是很少叫人失望,堪称名符其实的活字典了。
离县城不远处还有一个屈原故里,那个地方叫乐平里。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更是一九五三年在赫尔辛基公布的四位世界文化名人中唯一的中国人。现在很多人知道他只是因为端午节,可是在他的家乡就不一样了,人们敬仰他融入骨髓的爱国情怀,也在山水之间见证他充满诗意的绝世浪漫。在课堂上,无论是作为语文老师还是历史老师,只要一讲到屈原,爸都会滔滔不绝,他会讲屈原的盖世才华满腹经纶,也会讲他的怀才不遇颠沛流离。
屈原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了,可是在家乡人的心里,他从未离去。我们小时候,他就象是邻居家的一个大哥哥陪我们长大,每到橘子收获的季节,我们就会想起他的《橘颂》;等我们长大了,我们会读他的《九歌》和《天问》,这时他又象一个智慧的长者引领我们勇敢地走向更加广阔的前方。
四
可是爸还是想回家,而且这一次他是胸有成竹的。
一九七七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尽管我们三姐弟都还小,但是爸却从中看到了希望,他到处为我们收集当时不可多得的课外学习资料,从菲薄的工资中拿出不少钱为我们订《娃娃报》,订《儿童时代》,订《少年文艺》,后来又订《中学生数理化》。
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三个都没有辜负他的一片苦心,全部考上了大学,我更是到了他心心念念几十年的武汉,上学、工作、结婚、生子,一切都好象是顺理成章。
也是在这里我觉得自己终于真正理解了他对回家的渴望和痛苦。
记得上中学时我曾经问过他省城到底有什么好,县城到底哪里比不上它?他想了一下说,“可能是文化氛围吧!”当时的我脱口而出:“我们这里也有电影院啊,哪里差了?”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等你去了就知道了!”。
当我真正走在武汉的街头,走进一个又一个大学的校园,我明白了,当年的我真的是井底之蛙夜郎自大啊,这哪里是差一点点,简直就是天上和地下的区别啊!
我小的时候爸常说他中学的语文老师是闻一多先生的秘书,当时我以为他在吹牛,可是现在我信了。武汉大学的校园是李四光先生亲自带队勘探请人设计的,现在仍是全国最美的大学校园之一,这么美的地方自然是群英荟萃,闻一多先生就是当年的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能做他的秘书的人想必也是功底极为不一般的人啊!
一九八八年的暑假期间,因缘巧合我见到了一个爸当年读省立商业学校的同班同学,她对我说:“你爸当年是班里的团支书,成绩好,对人好,口琴吹得好,字写得好,尤其是算盘打得又快又准,喜欢他的人很多的!”,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的脸上笑开了花,好象沉浸在当年的回忆里,我突然有一种感觉,那些喜欢爸的人中间一定有她吧?
这么看起来,远离省城的爸牺牲的不仅仅是他极为看重的文化氛围,或许也有他尚未来得及开始的爱情啊!
五
好在我们历尽磨难的祖国大地上,改革开放的号角早已吹响,春风拂面阳光灿烂的日子就要来到了。
一九八四年的上半年,我们又搬家了。新家有四间房,是由一间教室隔成的,客厅的一面墙上还有一块完整的黑板。我们都很喜欢这个新家,不仅因为它很大,还因为这一次我们终于有了自来水,有了一台十四吋的黑白电视机。
一九八七年,全家人终于住上了学校新盖的楼房,虽说我们的房子在顶层六楼,但那是一套正规的三室一厅的房子,有专门的厨房和卫生间,还有两个宽大的阳台。在后来的日子里,家里还陆续添了电饭锅、洗衣机、冰箱、彩电、电风扇等家用电器,特别令人惊喜的是以前根本不敢想的电话也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日子真的是一天天好起来了!
当我们三个孩子都离开家以后,爸依然在那个小学(当时已经改名为实验小学)当老师,不同的是他的脸上时常有了笑容,他总是说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要享受生活了。
他不再提回家的事,好象很满意现在的生活了,随遇而安是他常说的一句话,到这时我才发现:爸以前所有对回家的执着其实是为了他的孩子们!他自己生活艰苦怀才不遇,都能忍,可是他想让自己的孩子们有另外一种生活,一种他认为曾经有过的幸福生活,那种幸福是他的父母给他的,他也想给我们。
他去那个偏远的小县城是工作是奉献,他是满腔热忱去建设新中国的,他骄傲他自豪,只是长女的意外夭折向他展示了生活的残酷,让他开始害怕,他胆战心惊生怕我们三个再有什么闪失。当我们终于长大成人的那一天,他如释重负,他解放了,这时他内心深处的乐观豁达再次展现出来。
有一次我们回去看他时,他故作神秘地说:“我今天去了附近的两个大城市,每个城市都有一百万人,你们猜是哪里啊?”那个时候县城才一万多人,哪里有什么一百万人的大城市啊!看我们实在猜不出来,他一下子哈哈大笑,“就是水月市和普安市啊!”我们知道他说的其实是水月寺和普安寺,就是县下面的两个小镇,每个镇也只有不到三千人。
归根到底,看来爸还是喜欢大城市的,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全是在那里度过的,那些记忆留在他的心里,此生是抹不去了。
六
一九九四年的七月,爸从县实验小学高级教师的岗位上光荣退休了。退休后的爸依然住在那个小县城,他不再急着回贵州,也不再想着回省城,他老了,不想折腾了。
可是命运再一次让爸不得不面临选择:由于国家在长江上修建三峡大坝,作为长江的支流,县城旁的香溪河水位会上涨很多,大量房子会被水淹没,其中就包括爸好不容易在五十三岁时才住上的那套近九十平米的三室一厅的房子,整个县城将不得不搬迁到另一个地方。
家在哪里?家到底是什么?
是一个房子还是一个地方?是父母双亲兄弟姐妹还是夫妻子女?或者它就是一段幸福快乐的时光?
好象都是,却又好象还差一点什么。
也许那是一种感觉,是我们的祖先为我们刻在血液里的一种感觉:无论世事是多么的变化无常,心中自有一片桃花源,回家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努力奋斗把心中的桃花源变为现实的过程。
那个曾经晚上八点就漆黑一片的地方,现在到处是水电厂,不仅实现了本县一天二十四小时稳定供电,还把多余的电送上国家电网,再送到全国各地。那个闭塞落后到处都是文盲的地方,现在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率接近100%,爸的学生中甚至还有人后来成了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他常说,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相比于爷爷那一代人不得不经历的战乱频发血雨腥风,他有幸遇到了一个和平的好时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的生活水平持续提高,这一切都是因为党的政策好,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幸福过。
是的,象屈原那样面对着国破家亡、生灵涂炭,只能悲愤投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同样的,为了换取整个国家的暂时和平把美丽的女子送去和亲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祖国的强大,而这种强大不是凭空得来的,无数人为了国家的强大奉献所有,但他们无怨无悔。
七
一九九九年的下半年,爸和妈一起离开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县城,作为三峡库区移民,他们来到宜昌,住在一套租来的小房子里。
原来的家已经沉入水下,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本该安享晚年的他们决心在宜昌再建一个新家,只是这并不容易。
当宜昌的房地产蓬勃发展时,一个个漂亮的住宅小区拔地而起,爸也想买房,可是长期的低工资让他囊中羞涩,他几乎没有存下什么钱,和不断上涨的房价相比,国家给的移民赔款也是微薄的,所以多年以来只能望房兴叹。
好在国家没有忘记他,在他快八十岁的时候,终于把户口迁到了宜昌,八十岁时还享受到了国家每月五十元的老年津贴。
现在他是真的老了,视力严重下降,看电视都是一片重影;有一个耳朵也听不见了,但他还是常常用另一个耳朵听他最喜欢的一首歌:《大中国》,每当听见那一句“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他的脸上就会露出会心的微笑,有时他也会喃喃自语:“现在就只有台湾没有统一了,那里的人就不想家吗?”,怕他听不见,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声对他说:“放心吧,就快统一了!”。
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象他一样的人还有千千万万,他们为了祖国这个大家庭更加美好,一次又一次地奉献所有。
但是爸始终认为,所有的奉献都是值得的!
三峡工程完成以后,宜昌成了举世闻名的水电之都,也是中国的动力心脏,大大缓解了困扰中国多年的能源问题,令世界为之惊叹!
中华民族正大踏步地走在复兴的路上!
在这个地球上,很多地方还是饥荒频频、疾病丛生、战火纷飞,只有我们伟大的祖国,任凭风浪起,我自岿然不动。
就象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就象汪洋中的诺亚方舟,中国让世界看到了希望!
二零一九年新年伊始,习近平主席就台湾问题发表重要讲话,祖国统一指日可待!
遗憾的是:在举国欢庆新中国建国七十周年的人群里再也看不到爸的身影了,因为两年前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好在去世前一年,他终于住上了他的三个孩子为他买的新房子!
好在他长眠的地方是一个风景宜人山青水秀的地方,距陵园不远处就是他最爱的三峡植物园,那里聚集了三峡地区大量的珍奇植物,有四季盛开的鲜花,是真正的人间仙境!
曾经只是梦想中的桃花源,就要在中华大地上变为现实了!
这一次,爸永远地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