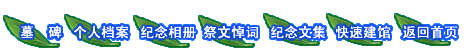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
1960年刚参加工作,父亲就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一直到2003年退休,父亲在教师岗位上工作了43年。
刚参加工作时,父亲教的是数学。几年后,因为师资不足,父亲改行当了语文老师。本来教的都是小学四、五年级的语文,后来三年级学生开始要求写作文,老师们因为觉得教小学生开始写作文比较费劲,都不愿意教三年级,父亲二话不说开始转教三年级语文,这一转,一直到退休。村里的小学,师资不足,每位老师都要兼多门课程,别的老师大多兼的同一课程多个年级,父亲兼的则是不同的课程,每次开新课,课任教师必然有父亲。正因此缘故,除了语文,我小学时的思想品德、自然、毛笔字、图画等等课程的课任教师都是父亲。
父亲深信知识改变命运。家里供不起父亲上学,父亲就利用课余时间,到野外的石场捡拾边角料,加工成碎石换回学费和生活费,直至完成学业。父亲这一信念转化成对我们五个子女的要求,几十年里,父亲母亲省吃俭用供我们读书,五个孩子都完成了大学教育。对城市里的家庭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在整个洋浦地区,前无古人,至今为止的多子女家庭中也还是后无来者。正因为这样,在农村家族势力盛行的年代,作为小家族的父亲母亲得到了乡邻们一直的尊重。为此,父亲一直在默默付出。甚至为了给正在武汉读大学的大哥筹够回家的路费和第二学期的生活费,父亲不管寒风凛冽,坐上小帆船到海对岸的白马井,卖血,换回的钱电汇给大哥。那是1984年春节前的腊月,我站在海岸边,看着那一叶孤舟在海浪中颠簸远去……
父亲一直认为,衡量语文学得好坏的重要标准在于作文的水平。不管教哪个年级,每周给学生布置一篇作文是家常便饭,父亲评阅和讲评作文的工作量比其他同事多上好几倍。对刚接触作文的小学三年级学生来说,这是个苦差事,我更是“苦不堪言”。父亲利用“职务之便”,给我开了不少“小灶”,除了班上正常布置的作文以外,日记、周记或其他各种题材,我的作文作业量比同班同学要多上许多。
感谢父亲,正因为父亲坚持的“小灶”,让长大后的我,不再害怕“爬格子”。
今天六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