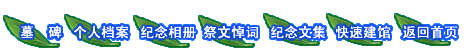杜甫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父亲是个普通人,没有杜甫庇护天下寒士的雄心;作为一位父亲,他的朴素心愿是给每个子女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婚后多年的父亲母亲为了结束租住村民房子的囧境,与二伯父一起在老宅基地上盖了一间30多平米的瓦房,用竹竿、破草席、报纸糊成隔墙,废弃的药品木箱拼接成门,一家住一半。瓦房边上用泥巴、茅草搭成的另一小间,则是奶奶的卧室、我家的厨房兼“餐厅”。每当下雨,只能用簸箕当伞,盖住“餐桌”,一家老小戴上草帽,品尝拌着雨水的“浪漫大餐”。我的童年就在这蜗居里度过。
七十年代中,二伯父去世,堂兄也到了结婚的年龄。为给堂兄创造结婚条件,父亲母亲决定搬出祖屋。几番奔波,一位远房亲戚半卖半送了一小块二十多平米的海边峭壁上的三角菜地,这是我们新的宅基地。接下来的几年,父亲母亲利用节假日和中午放学时间,到野外的石场捡拾废弃的石块,或者到荒地里挖泥,再借上牛车拉回来,肩挑手扛,搬到宅基地上,石块是建房的材料,泥土则用来填海造地。
1978年,40多平米的新瓦房建成,我们搬到了新家。父亲母亲继续在海边捡拾小块礁石,继续挖泥抬土,继续努力把峭壁填成平地。
几年后,后院盖了两间小瓦房,已经读大学的大哥终于有了自己的小窝,家里的厨房也终于告别了茅草房时代。直到这时,老宅与后院还有一米多的落差,需要爬8级台阶。
1986年,后院继续加盖了两间瓦房,三个姐姐终于有了一间共用的卧室,上初中的我也有了自己的升级版蜗居。
1998年,居住了20年的瓦房已经破败不堪。父亲母亲改扩建成了一幢占地近百平米的两层小楼,我们生平住上了楼房。
2010年,年过七旬的父亲母亲拆除了后院的瓦房,改扩建成楼房。除了技术活,父亲母亲仍然是亲力亲为,能省则省。后楼落成了,父亲母亲却连桌椅板凳都无力购买,三个姐姐共同购置了必要的家具。每当提起,堂兄便会说,那是小爹小娘用了一辈子的时间,省吃俭用,在黑板前用粉笔写下的楼房。
父亲最喜欢的“走马楼”成型了,父亲那个每个子女都有属于自己房间的朴素心愿终于实现了,但父亲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年迈的父亲劳碌过度,身体垮了下来。2014年中秋节,父亲摔伤,这时离他一砖一瓦建成“海边别墅”尚不足4年。
2015年,病倒的父亲不得不到海口和我们共同生活,从此,他离“海边别墅”越来越远。
今天五七,谨此铭记父亲为达成朴素心愿付出一生辛劳乃至生命的创业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