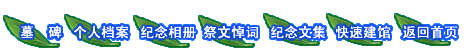再见母亲时,是中秋节前一天的早晨,她背对着门坐在里屋的床边上,低着头不知在想着什么,我快步走到她面前,她那因久病黄中略泛着青的脸庞在看到我时泪瞬间落下,滴滴眼泪化作把把利剑,插在我心上,我神情有点恍惚,怎么都和那个曾经精神抖擞,干活雷厉风行的母亲对应不起来。
母亲年轻时是什么样子我早已没了印象,在我家有一张她学生时代的毕业照片,穿着列宁服,梳着属于那个时代最流行的齐耳短发,没有出众的容颜,但不乏清秀端庄,紧闭略微上翘的嘴角透着一份青涩、倔强,暮年以后,时光把母亲打磨得如同一颗圆润发着暗亚光晕的珠子,青涩变成成熟,倔强依然还是倔强。母亲的照片如同时光隧道中的节点,将我拖入儿时的回忆。
我对母亲最早的记忆总是和吃有交集,第一次吃香蕉是在我四五岁时,一个冬天的中午,母亲叫起午睡的我,还在我迷迷糊糊时给我手里塞了一根香蕉,那时的香蕉用珍馐美味形容一点不为过,香甜可口糯糯的味道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长达十年之久,直到我再次吃上香蕉为止。我怀疑就是这次母亲将我的馋虫勾了出来,就此一发不可收拾,我对吃有了近乎极端的执着,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仓鼠有一比,家里根本放不住零食,一到寒假时,每天早晨我和哥哥躺在被窝里等母亲给我们发糖是我们最快乐的事,我们比谁的糖多,谁的糖纸好看,谁的糖好吃,妈妈有一个小柜子,在她高兴时总能从里面变幻出意想不到的零嘴,我为那柜子里的零食朝思暮想,魂不守舍,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把上面抽屉取掉,就可以从上面伸手下去拿到糖,哎呀,当时的那种兴奋劲难以言表,好像阿里巴巴发现大宝藏,但没持续多久就被母亲一顿“全武行”终结了事。母亲很会做饭,简单的食材只要在母亲手里随意变换,呈上餐桌的是美味佳肴,母亲可以把一顿普普通通的臊子面烹饪得从视觉到味觉都是一次冲击,红的萝卜、黄的鸡蛋皮、绿的香菜、白的土豆,喝着汤让人觉得世间美味也不过如此,我到现在也没学到母亲的真传,精心调出的汤和她调出的汤味道那是南辕北辙,不是一个味。
母亲会拉手风琴,会弹脚踏琴,我的童年就是在看着母亲拉着手风琴给跳舞的小朋友伴奏,而我站在旁边无比自豪中度过的,可惜手足几个没有一个遗传母亲的文艺气息,连基本音律都不懂。 但是我对绘画喜好是母亲启蒙的,母亲眼睛不大,可是观察事物精准到位,简单几笔就能勾勒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小动物,儿时,我让老爸给我画娃娃,老爸画的永远都是一个丁老头,可是笔到妈妈手里画出的线条总是让我脑袋瓜里充满想象力,妈妈的画不只是在纸上,还在中秋节烙的锅盔上,有熊猫吃竹子、有牡丹花开、有嫦娥奔月,还在姐姐绣花的图谱上,有玉洁冰清的荷花、有傲视霜雪的菊花、有飞奔雀跃的小鹿,在母亲的潜移默化下我由衷喜欢上了画画,遗憾的是从没有专业学过绘画,只会在本子上胡写乱画,在二十郎当岁时曾学过一段时间的画,终因不定性将画具束之高阁完事,但近几年想学绘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我也想学母亲的样子拿起画笔描天绘地完成自己一个小小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