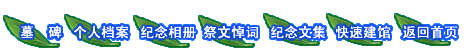我在家中排行第四,为纪念姬姓远祖取小名姬姑。1925年出生,三岁时在济南时得一场大病。后来听大人说父亲蒋继尹对我这个唯一的女儿十分宝贝,此次常常守在医院隔离室外,隔窗看着我。四岁全家随父亲从山东济南经梧州水路回家乡全州,遇土匪。同时落入匪手的还有在广西大学读书的堂兄朝清、朝沅、朝江。土匪觉得这么多人也是负担,同时也需要人回家报信筹款,于是在去往匪巢的路上我与母亲、三哥还有正在吃奶的五弟被放回,后来父亲竟被土匪撕票。
母亲回到老家,因为死了丈夫,被认为克夫,外家人又远在山东。父亲幼时,被长辈按惯例与数辈有姻亲的唐家定亲,因为长期近亲结婚,这位唐氏有精神病,父亲不喜欢。加上13岁就离开家乡,之后也因此从不回家,这位唐姓母亲也许受到刺激,病情更重。于是完全疯癫,整日端坐在一张椅子上,大睁着两眼,孩子见了很害怕。尽管这样,这位癫子奶奶才是正室,人叫七奶奶(爷爷在家族中排第七),母亲虽然带着五个孩子到家只能算小妾。蒋家是一个封建大家庭,未曾分家,五六桌人吃饭。三个媳妇轮流做饭。大房伯娘有丫头代为操作,二房伯娘农村出身,也有丫头。母亲在外面也是有几个佣人,而自己从不理会家务事的。现在这样到家,没有佣人,又是小脚,其艰难可以想象。全州吃辣,初来时一家人饮食都不习惯,只能将菜放到开水里洗一洗再吃。小孩贪吃,一次看见阳沟中有一个石榴,我去捡起,被母亲一巴掌打掉,我那时小,还不懂什么叫世态炎凉,倒是母亲伤心地大哭,可见当时母亲在家中的地位。我上小学了,住校,每周一上学,周六回家。当时男女同学不同住,女生住在乡公所头锁,由大姑妈(父亲的姐妹)管理。大姑妈有个三、四岁的女儿,我放学后就帮她带女儿,有点像佣人保姆。一起上学的有大伯的女儿巧姑。太姑妈很势利,对巧姑好,时常欺负我。为改善伙食我母亲每周一给我带菜,但是到了学校就会被她缴掉一半。经常无辜罚我的站,有一次我又被罚站,巧姑是个小孩子,没有成年人那些势利的做法,还一边帮我扇扇。母亲其实心很善,接济甚至收留穷苦人家。但是男人死了,在大家庭中饱受欺侮;全家连佣人都瞧不起,所以,母亲有时会突然歇斯底里发脾气。
母亲也许在大家庭中很压抑,就吸食上了鸦片,自称以前生病用此做药成瘾:她离不开鸦片,但是在大家庭中又不敢公开,只好请长工悄悄地去买来做成药丸吃。于是与这个长工接触比较多,家里不知道她吸食鸦片,家族长辈认为她不守妇道,母亲感到万分委屈,于是决意上吊自杀。上吊不成,就想跳崖。一次母亲在前面往悬崖上爬,我们几个孩子在后面哭喊,后来遇到一个砍柴的人才拉住她。尽管这样,母亲还是离不开鸦片,家里经济状况因母亲吸食鸦片而较差,甚至我上学的学费都成问题,四伯娘(康林之奶奶)之子朝清还接济了我一个学期的学费。我考取中学后,兄弟们也都大了,爷爷对我态度完全改观,我们在家中的地位逐渐高起来。
抗战时期,1944年日本对我国南方的几座城市狂轰滥炸,长沙大火,桂林紧急疏散,我随难民逃到重庆。当时难民太多,交通工具太少,火车上下内外都挤满了难民,事后我们回忆那单层的车厢从高到低共有五层:火车顶一层、行李架一层、椅子一层、椅子下一层、车轮杠上搭上板子一层。我们当时一分钱都没有,沿途靠当时还是男友的曾治品的大哥的生意伙伴接济,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到了重庆。到达重庆后,1944年冬天经人介绍到从南京迁来重庆的中央印制(造币厂)当点钞工。计件工资,工资仅够维持最低生活。在这里我认识了一批热血青年,其中有几个地下党,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抗战胜利后工厂要迁回南京,厂方计划把原来从南京带来的老职工带回,在重庆招的一批人就完全不管了,愤怒的工人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和行动,并且选我作斗争的副理事长。后来斗争取得成功,厂方答应发给工人一定的遣散费,大家庆祝斗争成功聚餐,还打了一个金牌给我作为奖励。工厂迁走了,我又一次失业了。我们准备回桂林,因为费用不够就把金牌卖掉了作盘缠。回桂林之后,不久就《广西日报》(当时桂林市是广西的省会)与男友曾治品登报结婚。
回到桂林,原来在四川与地下党的关系中断,此时北京有一个同学刘焱说有地下党的关系,于是我们就到了北京,通过它找到刘仁(解放后任北京市委副书记)。这时国民党接受了东北的阜新煤矿,缺一个简报社主编,刘焱就介绍我去了阜新煤矿,(文革调查发现了一个国民党特务部门追捕曾定之、蒋朝渊的通缉令,大概是当时的桂系与中央有矛盾,未予理睬,而我们竟完全不知道。)在阜新煤矿这段时间收入较高,生活也较稳定,第一个孩子晓新出生。 48年解放军解放东北之前,我们又离开阜新煤矿奔赴华北解放区。6月到解放区河北西柏坡平山华北军区司令部联络部(部长李英儒即著名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此时与党的关系再次接上。我们被送到华北联合大学(后改为华北大学)第一部培训学习,提高理论水平,结业后分配到华北财政学院。该学院后来取消,改为华北财委(主任委员薄一波),继而又改为中央财委(主任陈云,薄一波、马寅初、李富春都任副主任。)一直到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高岗当主席),我担任中央机关俱乐部主任。一两年后又回到国家统计局统计总署世界经济研究组搞统计工作。
解放初期,本来我已报名抗美援朝,因为怀孕不能如愿,1950年12月8日二儿子小平出生。1953年三儿子大建出生,1954年四儿子大军出生;1957年五儿子小武出生。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向北京要两千干部,我们夫妇俩人被派回广西桂林植物研究所。我在植物研究所办的植物专科学校担任教务主任,校长由植物所所长兼任,这个学校一共办了四年,先后培养了三百多名学生。这些学生中后来还出了两个研究员,桂林市园林部门的领导一度全部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植物学校停办后,我担任植物研究所图书馆的馆长。后来植物所把图书馆、资料室、广西植物编辑部合并为情报研究室,我在情报室工作,直到1986年按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离休。
(2011年7月时年八十六岁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