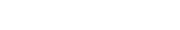九死一生逃出魔窟
华蓥星光 2021/5/12 14:56:00 浏览:479
九死一生逃出魔窟
--张泽厚在重庆渣滓洞“11.27”大屠杀中余生记
摘自《四川统一战线》金青禾文章
1949年11月27日,夜幕早早地把山城重庆罩住了。天,格外黑,地,特别暗。在这昏天黑地之中,似闻隆隆炮声把黑夜震碎,尤见道道火光将毒蛇猛兽烧成灰烬。魔鬼,在火光前发抖,深感末日就要来临;人民,在炮声中窃喜,盼着春天早日来临。
这一天,重庆歌乐山下的国民党监狱渣滓洞动荡不安。看守牢房的特务连,换岗频繁,他们把楼上牢房的“囚犯”一个个赶到楼下房间来。牢友清楚,黎明将到,特务们感到末日监头,妄图垂死挣扎要大开杀戒了。
在楼下的第四囚室里,六张上下铺的小床分两排放在十五六平方米的地上,屎尿的臭气和霉味使人窒息,昏暗的灯光从小窗射进,显得阴森潮湿。在最里边靠墙壁那张床的下铺,睡着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小个子中年人,名叫张泽厚。他也和其他难友一样,正面临着死神来临。
张泽厚,1906年生,岳池县赛龙乡人,毕业于上海艺术大学西画系。1930年执教于西南大学,当年7月学校被查封,他与梁伯隆等7名教授被捕。后保释出狱到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任组织干事,主编过《文艺评论》、《艺术周报》、《文艺新地》。1933年他因被上海市政府通缉返回岳池,先后在四川旅宜中学、国华中学任教。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因国华中学被查封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回岳池新三中学任教导主任。1948年8月他支持华蓥山武装起义,与其弟、地下党员张泽浩等人一同被捕,关押于重庆渣滓洞,受尽摧残与折磨。
一阵阵脚步声、呵斥声、枪托砸“犯人”的咚咚声、难友怒骂和交头接耳的嗡嗡声混在一起,把张泽厚从梦中惊醒。他揉眼一看,屋里来了不少人,大家睁着愤怒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门外、窗外。他尽快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悄悄地拍拍坐在床沿的难友:“张远静,为啥子要下楼来?”张远静忙俯下身子说:“上头通知,楼上的人一律下来,等会儿好点名。”他听了睁大双眼:“什么点名?用机关枪来点?唉,怪不得这几天......”张远静伸手按下他抬起来的头:“小声点。”他朝木条子门外一瞄,全副武装的国民党特务在外面的坝子里奔忙。他转过头来在张远静的身上拍了拍:“你看,我们即将见阳光,却要被天亮前的冷雾毁了。我们的日子就在今晚。”很快,牢房的前窗同时伸进三只乌黑的枪筒子,顿时机枪如炒豆子似地乱叫着。
小床的木板被一个个洞穿,屋角的屎尿罐被打烂,囚被上大洞小眼,墙壁上泥土直掉......难友们纷纷倒在血泊中。他眼睁睁地望着魔鬼们横行,看到难友们一个一个地倒下。他床边的张远静一抖,伸手没抓紧床枋,头一啄,身子猛地从床沿滑在地上,没了声息。又一阵密集的子弹从张泽厚头上飞过,打到墙上,大砣小砣的墙壁泥块纷纷落在他的床上、身上,压住了又烂又黑的囚被。他以为自己的一切连同生命也和难友一样,被特务们夺去了。他脑子一动:“冲出去,拼一拼。”但他马上静了下来:“外面这样多敌人,特务防守又严,内外好几道岗哨,自己赤手空拳冲出去还不是送死”。然而,生的希望给了他无穷无尽的力量,犹如干渴的心田撒下一阵细雨。他想到抗日战争中有不少中国同胞躺在死尸中从鬼子的利刀下活出来的事,于是决定用装死的办法与敌人斗争。
前窗的枪声停了,后窗又响起了枪声。他听到隔壁第三、第五室的难友随着枪声高喊:“共产党是打不死杀不完的!”“共产党万岁!”随后敌人的枪尖从他头顶伸过来。他在特务的枪口下忍耐着,悄悄地将自己连同被子向墙边靠了靠。这样,即使枪口从后窗向下斜射,他也不会被击中。
不久,一道白亮的手电光射进了四号囚房,他听到哗啦一响,3个家伙鬼头鬼脑地走进房来。他们从外到内、从上到下地察看着,步步向他逼来。他的心跳得更加厉害,五脏六腑直向上提。他躺在那里,一股后悔的情绪堵得难受,他恨自己为何犹豫,不趁特务歇枪之机冲出去,这下好了,只有等特务在他身上补上几枪了。怦怦连响两枪,刽子手向第二床那个难友打了一梭子弹,嚎叫道:“妈的,你龟儿还在动!你动,我看你再动!”接着又用枪筒子砸难友的头。张泽厚看到难友血肉模糊的手,在床沿上抓了几下,留下手印就垂下了,他忙把眼闭着。特务向他靠近,他感到全身发凉,压在被子中的手一下握成拳头,他准备趁这家伙不备,当胸给他一拳,即使打不死这个恶魔,也总比让这家伙如此便宜地把自己送走强。特务的手电在一床上扫射,那家伙嘴里又不干不净地骂了句什么,紧接着怦怦怦一连几枪,听到“唉哟”一声,又一个难友的生命被魔鬼夺去了。他听到这几声枪响如注射了镇静剂,心情反倒显得平静了。白色的手电光如毒液四溅,扫射在张泽厚的床上,从脚到头,越过被泥土压住的身子,向他头部移来。他微闭着双眼,隐约看到特务拿着手电筒在他的鼻前。他知道特务在试探他是否还活着,赶忙闭着眼屏住呼吸。“这下真的完了。”他不无遗憾地在心中感叹。“死了,已经死了。不死这堆泥巴也把他压死了。”另一个特务对打手电的特务不满地说。这时外面突然响起哨声,特务们慌忙退出四号牢房。张泽厚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如在热锅上熬了十年那么长。他的脸被憋青了,手脚软得没力,特务刚退走,他就瘫在床上,周身湿漉漉的,冷汗已湿透了内衣。
枪声稀稀落落,牢房外的特务们奔忙着。一会儿楼上楼下又响起叮叮咚咚的震动声。掀桌子,摔东西,将汽油之类的东西泼洒在楼板上......不久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那哗哗啪啪燃烧东西发出的暴裂声使人心惊肉跳,敌人最毒辣的一手使了出来,那就是妄图让渣滓洞和它的“囚犯”们一同化为灰烬。
火势越来越大,烟雾越来越浓。特务小分队眼见屠杀革命者的任务已经完成,纷纷逃走了。
张泽厚睡在床上,心乱了:再也不能这么活活地等死。他把衣服一穿,艰难地走到门边,用力推门,可外面已经上了锁。他急了,忙转过身来,发瑞身后还有一位受了伤的难友。他急中生智,小声说:“我有办法,跟我走。”他又走到门边,用脚轻踢那木条子门,木枋未断。求生的本能使他力气倍增,他用尽全身力气再次向木条子重复踢去,只听“嚓”的一声,酒杯粗细的木条断了。在踢断几根木条后,他拉了身后难友一下:“跟我来。”说完俯下身子,从木条子门下钻了出去。难友也随后出了牢门。他转过头一看,女牢房前烟火正浓。他正考虑到什么地方去躲时,突然从对面岗亭扫来一排子弹。他机敏地顺势倒下去,跌在六尺多高的阶沿下的阳沟里。后面的难友不幸被子弹击中,倒在阶沿上。
阳沟地势低,电灯光及火光都照射不到。他以为自己死了,可又觉得神志很清醒。两尺多深的阳沟中,又臭又脏的污水、污泥、粪便、死老鼠、乱石、枯枝烂叶......什么都有,他睡在里面,棉衣、烂裤被湿透,禁不住冷得身子直抖,牙齿打架,伤痛也一阵阵向他袭来,如有无数钢针刺向大腿。他全然顾不得冷,一边抬头张望,一边思索。“往茅房(厕所)里爬。”有人向他喊道。张泽厚抬头一看,是楼上一室的难友刘振美。见到死里逃生的难友,他血在涌、劲在增,使劲用手肘往茅房的方向爬去,每爬一步都觉得要耗去全身力气。阳沟水越来越深,臭气也越来越憋人。
阳沟的转角处有一口水池,水池里的竹筒把水引进附近一个木桶,专供“犯人”们洗屎尿罐子用。此时木桶的水已满,溢出的水流到地上,再流到沟中。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爬到木桶边,双手吃力地撑起身子,一点点地向上,好不容易才爬上了地坝。
不远的茅房像位亲人,在热情地向他招手。他爬一阵,滚几滚,身后留下了血与污水的痕迹。
特别小分队走后,守卫渣滓洞的特务连的魔鬼不时从岗哨里挖出头来扫一眼,然后像乌龟一样缩回去。牢房先是经过枪杀,后又进行清洗,再后用火焚烧,他们以为犯人们早已斩尽杀绝,只等上司撤离的命令一到即可拔腿逃命。张泽厚趁特务小分队已走,守卫的特务坐等撤退,牢房边无人巡逻的机会,奋力地向着茅房爬去。五米、四米、三米、二米......他终于把沉重的身子移进了小小的茅房里。
他爬进茅房,发现4个难友正挨着墙坐着,尿槽边还斜趟着一个难友。他说:“刘振美,不行,非下茅坑不可。守卫连的人一来,我们......”果真,从岗哨亭子里传来懒洋洋的声音:“喂,再到各处去看看,有没有人......”这声音使在茅房里的6个人都吃了一惊。监狱里的茅房坑位没有隔开,由木板铺就,木板下面是一个倾斜的屎尿槽,槽底与木板相距三尺来高。屎尿槽把大小便送到厕所外的粪坑中。张泽厚让几个难友下到屎尿槽后,才最后一个在进门的第一个蹲位下面藏身。
他们知道,重庆即将解放,他和几位难友无论如何也要等待亲人的到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几个难友在粪槽里冷得周身冰凉,颤抖不已。“出去吧,在这里等死呀?”有难友经受不住寒冷侵袭,小声提议。“不行,渣滓洞这鬼地方敌人防守严,岗位又多,出不去的。”有人小声反对:“还是另想办法吧。”
“等!等这些乌龟王八蛋滚了再说。”刘振美道。一声哨音打破寂静,特务连魔鬼们的杂乱争吵声,在坝子里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叩击在难友心上。只听一声高叫:“再清查一遍!”这狼嚎似的叫声如一把刀刺向6个难友的心,难友的心猛地提到嗓子眼。几个特务走进茅房,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们把枪栓拉得哗哗响。
透过茅厕蹲位木板的缝隙,张泽厚看到有两个特务正从他头上走过。走在后面的那个家伙踩得木板直打颤,泥土、灰尘直往他脸上掉,有几粒沙子落入他的眼睛和耳朵。他忍耐着,一动不动。哒哒哒随着一阵枪声,粪槽里火花四冒、大便飞溅,一股股殷红的血流进粪坑,难友们怕暴露目标,连哼都没哼一声。张泽厚的手掌被子弹打穿,左腿连中五枪,他只感到周身的血直往外涌,四肢麻木,不久就失去了知觉。
不知什么时候,微弱的声音把他叫醒:“张同志,你......可以出去了......特务们走了,我不行了......”他听出来了,是刘振美!就躺在他近旁。“不,我们一起出去。”张泽厚不知哪来的精神,大声地叫喊着:“好容易等到这机会。”“我......托你......出去,把这些吃人的豹狼的罪恶......揭露出来......让人知道......”刘振美的声音小了,“你多保重......啊......”他连叫几声刘振美,都无回音。他知道刘振美已经牺牲了,止不地泪水涌出来,滴在浸满鲜血的粪槽中。这时他想叫喊,可喊不出来,他想冲出去,却一点也动不了。双手双脚都受了伤,只有脑子是清醒的。“唉。”他叹了一声,“再不来人我也会死在这里了。”
不知什么时候天已大亮,睁眼看看死去的烈士,张泽厚身子仍然动不了,只能望到刘振美和那个辨认不清的遗体。他躺在那儿昏过去又醒来,醒来又昏过去,就这样在茅坑里度过了一天两夜。第三天早晨,天还没有大亮,一阵脚步声打破黎明的寂静,他的心又咚咚地跳着。有人一脚踩在头部上面那块木板上,停了好一阵。呼不呼救?喊吗,是好人还是坏人弄不清楚,不喊吗,这机会他已等了好似一个世纪这么长,倘若失去也许不会再有。来人见茅房内毫无动静,欲退出。此时他大声地喊:“喂,老乡,快来救我。”来人问:“你在哪里,我怎么救你?”“你把进来的第一块木板扳开,把我扯出来。”他告诉来人。来人是个黑大个子,按照他的办法把他拉了出来,放在外面的坝子里就慌慌张张地跑了。来人走了,他被遗弃在坝子中,寒冷、饥饿、伤痛一齐向他袭来。他再次昏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时,已躺在一个汉子的手里。他见这身影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他看看天,天是这样的蓝,阳光格外耀眼,再望望四周,山野变得亲切起来。汉子的面孔很和善:“太对不起你了,我把你从茅房里弄出来,找不到往哪儿送,才去找的解放军,所以耽搁了这样久。”“谢谢!”张泽厚太激动了,用尽全身力气,可声音却小得很,一股热泪涌出来。外面的汽车发动了,他被黑大个抱起,一步步向渣滓洞门口走去。
在这次大屠杀中,渣滓洞关押的260余人(中央电视台在2004年2月6日报道为331人)仅侥幸逃出17人,张泽厚是其中的一个。他身中8枪,受伤9处。被解放军治好后,曾任川北大学副教授兼政治教研室副主任、南充市文联主席、民盟南充市委委员。川北大学撤销后,任四川师范学院副教授、民盟支部主委。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判刑20年,后释放。1982年被平反,任岳池县政协常委。他著有《伟大的政治》、《花与果实》、《旷野》、《艺术学大纲》、《青纱帐》、《乡居杂感》、《怒吼吧!中国》等诗歌、小说、教材等书籍。张泽厚1989年8月20日病逝。
- 暂无评论!
- 发表评论文章评论(共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