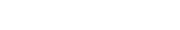艺术评论家
华蓥星光 2016/5/4 15:20:00 浏览:572
艺术家是自己国家、自己阶级的感觉,是它的耳朵、眼睛和心脏;他是自己时代的喉舌。
一【苏】高尔基
1931年夏天,张泽厚从法租界牢房被保释出来后,没有工作,生活困难。老师沈学诚决意帮学生渡过难关,他将自己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今南京艺术学院)担任的课程拿出一半推荐张泽厚去上,自己再去找新工作。张泽厚就这样在沈学诚的力荐下,校长刘海粟、教务长王济远接纳了他,他得以成为上海美专的教师。
当时上海美专人才济济,名人成堆:张大千、潘玉良、潘天寿、黄宾虹、谢公展、王济远、傅雷等都是名声在外的名牌教授,校长刘海粟(1896-1994)更是不同凡响,他作为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拓荒者和创始人,格外引人注目。在美专的众多同事中,张泽厚交往最多的当首推恩师沈学诚(沈西苓),其次便是国画大师张大千(1899-1983)与西画名家王济远(1893-1975)。张大千是四川内江人,难得见到同事中有四川老乡,加之二人都曾赴日留学学习绘画,相似的经历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他自然待张泽厚亲热有加。王济远早在1929年就见识过张泽厚的文笔,有过愉快的合作,他赏识张泽厚的艺术理论造诣,乐于提携这个艺术新人。
正是在和这些艺术大家的频繁交往中,让张泽厚倍感压力,他不敢大意,更需加倍努力。当时学校教材奇缺,谁上课谁就得自编讲义。张泽厚只得暂时减少参加“左联”活动,也顾不上办杂志,专心致志地编教材、站稳三尺讲台。他在编写教材时极为认真,立志结集出版。1933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了他的讲稿,这部专著就是著名的《艺术学大纲》。
《艺术学大纲》一问世,迅即得到了理论界的一致好评,“被公认为是第一部中国人撰写的以艺术学命名的的专著”。理论界将该书视为中国艺术学的奠基之作。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学术界更是对张泽厚的《艺术学大纲》为中国艺术学学科创立所作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凌继尧教授在《中国艺术批评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一文中指出: “而中国第一部以艺术学命名的著作,则是张泽厚的《艺术学大纲》,该书于1933年由光华书局出版。”(摘自《江西社会科学》为2001年11期)。
华侨大学音乐舞蹈学院陈凯丽老师也在《艺术理论课程的新音-评郑绵阳《艺术概论》一文中肯定《艺术学大纲》的奠基作用:“19世纪末随着西方美学、心理学等新兴学科传入中国,推动了我国的艺术学科建设和发展。1933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张泽厚的《艺术学大纲》是目前见到的我国最早的艺术专著。”(摘自《人民音乐:评论》2010年第9期)。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池瑜则在《廿世纪上半叶上海之美术研究概评》一文中强调: “在艺术理论方靣,丰子恺编译了《艺术慨论》(为立达学园给学生上《艺术慨论》课程编写)、俞寄凡出版了《艺术慨论》及张泽厚出版了《艺术学大纲》,这也是我国学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早出版的艺术基础理论方靣的著作。”(摘自《新浪博客》2O13年4月1日)。
中国文化部付部长王文章则在为《中国艺术学大纲》一书撰写的总序中,提到了那些开创中国艺术学的学者所作的贡献,他指出:“据现有资料,“艺术学“的学科名称,在我国初始出现于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俞寄凡译日本黑田鹏信的《艺术学纲要》一书,此后中国一些学者相继在文章著述中使用“艺术学”这一学科称谓。如宗白华从德国留学回国任教,即以“艺术学”为题在大学留下讲稿。此后,张泽厚于1933年由光华书局出版了《艺术学大纲》,陈中凡1943年9月在《大学月刊》发表《艺术科学的起源、发展及其派别》的论文,阐述作为学科的艺术学和艺术科学。”(王文章:《中国艺术学大纲》总序:《中国艺术学的当代架构》,三联出版社)。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仲呈祥教授也在《艺术学成为一级学科彰显艺术自觉、自信、自强》一文中提到了当年学科开拓者的贡献:“艺术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美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20世纪20年代开始被引入中国,滕固、宗白华、张泽厚、马采都曾使用“艺术学”这一学科名称,并以之为题撰写相关文章,讨论艺术学的研究对象等问题。但直到90年代,艺术学的学科地位才在中国得以确立。”
学者李心峰在《艺术理论“十五”回顾与“十一五”展望》一文中强调了艺术学开拓者们的贡献:“在20世纪前半期对现代形态的艺术理论、艺术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一批理论家如宗白华、朱光潜、蔡仪、丰子恺、滕固、马采、陈中凡、汪亚尘、俞寄凡、张泽厚等人的论著、文章受到人们的重视和研究,一批研究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和艺术学史的论文陆续发表。”
除上述学者外,还有一些学者对张泽厚的《艺术学大纲》作了更为详尽的深入研究,探讨该书的理论架构。这些学者中以陈池瑜、孙士聪、刘悦笛最具代表性。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陈池瑜教授在《廿世纪上半叶上海之美术研究概评》一文中肯定张泽厚《艺术学大纲》的“进步性”: “基本上是用唯物史观来解释艺术”,他强调指出: “至于张泽厚的《艺术学大纲》,则基本上是用唯物史观来解释艺术,认为艺术受着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因而艺术的变动基于经济生活的变动,艺术的任务就是认识生活,组织生活,促进社会合理发展,艺术起源于劳动,这些观点当时都带有进步性。该书1933年由光华书局出版。”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孙士聪副教授在《影响与对话》一书中高度评价《艺术学大纲》在学科创建中的历史地位,称赞该书的论断“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富有眼光的”。他指出:“1933年,张泽厚出版了一本名为《艺术学大纲》的书,该书“第九讲”在谈到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征时涉及艺术生产问题,认为艺术生产与其他生产明显不同,它不是“以机械的方法无限的制作出来”,但仍属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很特别的产业部门”,因为“在资本制度社会之下,艺术的作品,虽不是完全基于他们的天才和教养,但是他们的作品,无论如何,总是想以金钱来换掉或估计它的价值的。这就是艺术的商品化,这就是艺术的巨量生产的特殊现象”。这里不仅指出艺术生产与一般生产的不同,而且初步意识到艺术生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化现象,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富有眼光的。。。。。。
至于张泽厚是否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商品化进程是在该书出版50年后才开始起步和迅速推进的。这样看来,张泽厚考察艺术生产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还是指向于文艺对于当下社会现实的实际功用的,这从他在《艺术学大纲》第九讲最后的呼吁中可以清楚看出:天才的艺术家要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洞察社会的变革和新的时代的到来”,彻底地改变自己的意识而“效忠新的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室刘悦笛副研究员断言《艺术学大纲》“被公认为是第一部中国人撰写以艺术学命名的专著”,他在《从艺术学的“中国化”到中国化的“艺术学”》一文中对该书作了详细介绍,认定该书“表露出“中国化”的艺术学体系从创建时期就己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刘悦笛博士指出: “张泽厚1933年在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艺术学大纲》,被公认为是第一部中国人撰写以艺术学命名的专著,书名还是由柳亚子所题写的。该书分为十讲,分别是提出艺术与理论皆来自生活的《艺术理论值前提条件》;指出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艺术的起源》;分析艺术发展受到生产力支配的《艺术的发展》;对艺术进行自律与他律两分的《艺术的至上主义与功利主义的解释》;说明艺术隨社会关系而变的《艺术的变革与倾向》;阐明艺术以促进社会为目的的《艺术的目的性》;证明艺术渗入社会生活的《艺术的意义》;讲解西方艺术思潮缘起的《艺术思潮的社会背景》;区分宗法时代、封建时代与资本工业时代的《时代给予艺术的特质》;辨析艺术与宗教、哲学和(自然的社会)科学关联的《艺术与他种科学》;无论从大纲的整体体例结构还是具体的思想内涵来看,《艺术学大纲》都表露出“中国化”的艺术学体系从创建时期就己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即使今日仍使用这本专著为艺术学“教育藍本”也是具有极大参考价值的。”(摘自《艺术百家》2013年第4期)。
刘悦笛还在《深描20世纪中国艺术文化学》一文中对张泽厚的开创性学术成果进行剖析,他指出:“将艺术视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并考察了它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在《艺术学大纲》那里还是相当早的。实际上,越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人们就越来越将艺术这种文化形态看着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这己经预示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艺术社会学的趋向即将取代艺术文化学探索的主流位置。”张泽厚提出“艺术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这一论断深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这一论断判明了艺术学的发展方向,从而较早确立了艺术学的理论基础。围绕这一论断,张泽厚特别强调艺术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张泽厚指出: “艺术不仅与宗教、哲学及社会的经济基础有关,而且它与政治、法律、道德、风俗等社会意识形态都有密切的关系。”(刘悦笛:《深描20世纪中国艺术文化学》)张泽厚对艺术与其他社会科学关系的分析无疑是开创性的解决了艺术理论的又一重大课题,解决了长期困惑着艺术理论界的疑团。显然《艺术学大纲》在促进中国艺术理论的健康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而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和充分肯定。
《艺术学大纲》一书是张泽厚被迫离开上海后,委托老师、“左联“作家沈起予联系光华书局出版的,沈起予还依照张泽厚的嘱托,特地邀请著名诗人柳亚子为该书题写书名,可见其用心良苦。
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沈起予既是张泽厚的老师,又是亲密的“左联”战友,张泽厚的诗歌《伟大的开始》一问世,沈起予就在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上撰文予以高度评价。沈起予从1928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创作了《火线内》、《人性的恢复》、《残碑》、《飞露》、《我们七个人》、《洒场》等小说。他和妻子李兰又都是翻译家,译著有《欧洲文学发展史》、《艺术哲学》。沈起予先后作过《光明》半月刊主编、《新蜀报》、《新民晚报》副刊编辑、上海群益出版社主任编辑,对出版界甚为熟悉。
正是在沈起予的鼎力支持下,《艺术学大纲》才能顺利面世,可这部颇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却成了张泽厚告别艺术界的封山之作。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刻,张泽厚与其他爱国青年一样,意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己有责任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冲锋在前。他在中国共产党和鲁迅、李初黎、朱镜我、潘梓年、冯乃超、冯雪峰、丁玲、沈起予、沈学诚等“左联”作家 的影响下,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弃画从文、为抗日救亡呐喊的作家道路,从一个美术教授变成了著名的抗战诗人。虽然离开了艺术界,但他在艺术学领域内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对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引领、开创作用是举世公认的。
张泽厚在上海美专授课两年(1931年9月-1933年4月),深受学生欢迎。却因从事“左联”革命活动而被上海政府当局通缉追捕,不得不干1933年4月离开上海美专,远走四川避祸。
(摘自张良春、张昕宇著《张泽厚传》第五章)
- 暂无评论!
- 发表评论文章评论(共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