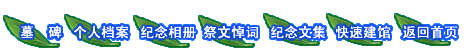我的母亲
母亲的娘家离我们家不远,就十里路吧,叫西番岔,村里大部分都是杨姓,都是一个家族的人,听母亲说,她娘家旧社会很富有,是远近闻名的富家,在外祖父的主持下,分工明确,男主外,女主内,把一个大家庭打理的是井井有条。听母亲讲,那时候的外公兄弟几个都很勤劳,只可惜我没有见过外爷,只听说外爷头发少白,眼睛高度近视(或许我的眼睛就是受了外家的隐形遗传)。外婆也是来自于临洮骨头沟的大户人家,我的记忆里是一个小脚,大个子,身板很硬朗,记得小时候我很捣蛋,受过好多次姥姥的教训。至于更远的外家族系与家史,就更不知道了。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想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的日子会大打折扣的。
母亲出嫁应该是很早的,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只小我两岁。我有六个姐姐,一个哥哥,我是“垫窝”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三十八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记忆中的小时候,老听母亲说,你爹在街上信用社当干部,我老是想象街上是个什么样子,是不是向我去过的我们村上的那地方一样,有口打口井,井台周边有很多房子,父亲可能就在其中一个院子里上班,我想了很久,就是想不出信用社是个什么样子,看到念中学的姐姐们都去街上上学,且能和父亲住在一块儿,心里很是羡慕,想着赶紧长大念中学了就能和父亲一块儿住了。
记忆中的小时候我们家全靠母亲独力抚养我们,父亲只在农忙季节才会看到骑着自行车回家帮忙,我们小孩子由姨奶奶帮忙照看。母亲除了要干农活外,还要给全家人做饭洗衣服,喂猪喂鸡,每每都是在夜里微弱发光的煤油灯下缝补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像个“拾粪叉”一样,褶口满手,是鲜红微肿的。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每次从农业社上工回来,背篓里总是装着满满的驴粪和柴草。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和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新的桌椅都是舅舅给我家打的,旧的一个双头柜和抽柜是父亲兄弟俩分家时分的,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一点尘土,抽柜上摆的一排酒瓶子总是明灿灿的发着光。门前,父亲栽下的一颗槐树年年夏天开许多白色的花,一出门就能闻到槐花的香味。
小时候的记忆大部分时间是和哥哥玩耍。姐姐们出嫁的出嫁了,念书的都在街上念书,记得每天早上都能听见六姐在哭,说母亲叫她起床迟了,跟不上上学时间了。三九寒天,天亮的迟,母亲都是把我们每天早上送到山顶,然后再看着我们下山,到山下了,大声喊“妈,你回去吧”,母亲才回家赶紧做事。
有客人来,无论家里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烙点油馍馍或做一碗长面去款待客人。舅父那时候是木匠兼皮匠,经常来我家做活,记忆中老盼望舅舅来,就有好吃的吃了。有时候遇见父亲回来,父亲和舅舅还要喝上几杯酒的,记得那时候他们划拳喝酒很是羡慕,就偷偷的喝上一杯,现在都记得,好像烧的跟刀子一样,从嘴里一直辣到嗓子里。
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都会蒸大馍馍,蒸大馍馍时她会放点明矾,蒸出的馍馍又大又好看。然后亲自去贺吊或者让我们大一点的姐姐带我们去,到如今我好客的习性还未改,因为自小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母亲活到老,辛苦到老,到现在八十多岁了都还是闲不住。她最会吃亏,小时候老给我们说:“娃娃,记得,吃亏是福”。给亲友邻居庄上人帮忙,老是记得她围着一件蓝色围裙,在厨房里帮忙,我看到肉就馋了,就会跑到厨房里拉着她的围裙不肯走,她会赶紧切一点肉放到我嘴里,说:“赶紧走,别人看见笑话尼”。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从小到大没见过她和别人吵架。小时候记得姨奶奶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我默默地跟在她身后,眼泪一直在流,现在想起来心里都是酸酸的。
从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十几位老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老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中学毕了业的时候,靠父亲的脸面,我进了银行工作,记得要去上班了,母亲连夜为我缝制了新的被褥,又起早给我烙了猪油合子,给我装了半书包,生怕是我会被饿坏一样。父亲送我走时,她只说了句:“上班了,做银行人,千万不敢拿别人的钱,不要给你爹脸上抹黑”,一句话终生影响着我。
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哥哥,因为八零年包产到户后,家中没有劳力,哥哥中学毕业后再没有去读书,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哥哥共同撑持的,所以每每说起哥哥,母亲的脸上总会露出一点亏欠之情,所以,后来的母亲都是尽心尽力,任劳任怨帮哥哥把三个孩子拉大,也算是尽了她老人家的一片心意。
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现在,母亲已远离我们而去,十月一了,我想念母亲。。。。。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至今去天堂已近百天,作为儿子,心有不甘,心如刀割。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二零一九年十月初一日克俭于雁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