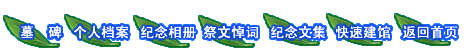2025年春节过后,在珠三角某城市的表哥发来微信,说我发表在《文化寻邬》的那三篇文章被他村里的叔叔发到群里,我颇感意外。同时,我读高一时的同桌以新手机号添加我微信,网络重逢的他转手也发了那三篇文章的截图。
《寻乌书园,一方人杰地灵的世外桃源》《小镇往事》《大年三十,我见到了阔别30多年的启蒙老师》均写于2020至2021年。三年来经历太多事情,本来此三篇文章已慢慢进入记忆深处,没料想在今年2月被群发引起了关注。几日后,教过我初三语文的黎红明老师也发了一张截图给我,来自他与平远教育界的老友知己群,同样是这三篇文章。红明老师说群里很多人都推崇我,我没想到有这个评价深感惭愧。桃李芬芳的他可能不记得了,初三那一年,他给我的几篇作文都打了高分并让我在课堂上朗读。
但三篇文章中,显然《寻乌书园,一方人杰地灵的世外桃源》更加受人关注。这不,村里的赖名金兄弟在群里说,平远的一位老局长看到此文还专门转发给他。用名金的话说,我给村里做了一件积德的好事,让更多的人知道了书园。也有寻乌的乡人说,我写的是“书园文化”,让他了解了岽背的文化内涵。四年前,借这篇文章,我重新回到乡亲们的视野并加入了村微信群。只是,村里已没有多少人认识常年在异乡的我;知道我乳名的人也越来越少,这让我珍惜,因为听到这个称呼会让我瞬间想起去世快20年的父亲。
说来惭愧,我的“名声在外”不是在书园和寻乌,而是在千里之外的江西黎川。十年间五到黎川、五十多万字的记载让我被许多黎川人所知悉,甚至旅居海外的黎川人。这期间我到黎川的次数,比我回书园的次数还多,因为我用最虔诚的心在黎川的每一个角落追寻爷爷潘明光的足迹。直到今天,这一追寻都没有停止,也不会终止。书园是我的人生起点,虽然与坪地合并后改为“书坪村”;但在我的内心,书园带着书香的名字将永远存在、历久弥香。正是在这种氛围之下,我萌生了再续书园故事的念头,讲述自己人生与书园的三个阶段,以及与之蕴含的家族历史和对亲人纪念。
第一个阶段,少年时期的“两栖生活”。小时候,我经常往返于书园与平远之间。众多的寒暑假和春节,我都是在村里度过的,那是一段亲情陪伴的岁月,陪伴的是那相依为命的继祖母和叔叔。我在村里的小学读了半个学期后被父亲到送外婆家,转到仁居中心小学从头读起。寄居在外婆家,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在陌生环境难免孤独和感到无助。前两年,有人经常看到放学后的我在傍晚的仁居河岸边打水漂。但庆幸的是,我遇到了一位优秀的的班主任,她就是我在《大年三十,我见到了阔别30多年的启蒙老师》提到的冯惠芬老师,让我加快适应了环境的改变。
从此,从仁居回到书园,我就变成了“客人”,继祖母和叔叔不让我干活,打下手的杂活也轻的。我成了继祖母的生活调色板,让家里多了一丝生气和活力,当继祖母和叔叔发生矛盾吵架的时候,有我这个调和剂在很快就可以和解。我去找左邻右舍的同龄人玩,大人小孩都在忙我帮不上还尴尬。于是在那些时候的暑假,我成了捏蜻蜓和抓蝴蝶、小蜜蜂的小能手,屋前屋后都留下我的脚印,简单得来也快乐。
但插秧、割禾、打谷的活我都干过,认真起来亦似模似样。唯一的特权,就是我可以拿着簸箕在田里找五彩斑斓的庞皮癞(又称斗鱼,对水质要求高),田里进水的小坑里一捞一把活蹦乱跳,养在瓶中爽心悦目、成为童年难得的乐趣。40多年前的村里没有电灯,每家每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政治经济学里那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傍晚时分,人们陆续回家。每一条回家的路是那么狭小台阶又多,看着大人们流着汗挑着一百多斤重的两箩稻谷、踩着二三十米高的石条路,我心里总有点担心怕他们滑一跤。我的叔叔沉默寡言但吃苦耐劳,被人戏称“小型拖拉机”,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命运作弄的他其实私下读过不少书,内心十分丰富。
收音机成了村民一天闲余时间里消遣和娱乐的好帮手,叔叔也有一台,这台破旧的收音机陪着他度过无聊的长夜和半生。村里山势虽高,但可以收到梅县和福建的电台,我从隔壁人家那里听过不少客家山歌。孩子们要帮家里放牛、割草和喂鸡鸭,也没什么玩具,箱子里那些为数不多的连环画,如今应已难找到踪影。我在村里看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是《刘三姐》,虽然在平远已经看过,但我依然拿着小板凳跟着大家去占位、凑热闹。这部电影选得好,如果是放《牧马人》《芙蓉镇》《活着》,那就看不明白了。
两栖生活的环境对比,让我学会观察、知道村与镇不一样。老人们说,村里你看到的天就是四周山岭围起来的那一块,要再大就得站在高处眺望那青黛色远峰如波浪般延绵的天际。圩镇上则有医院、邮局、信用社、百货店,县城里的人家还有电视机、自行车。对于村里人家来说,都明白只有让孩子努力读书、跳出农门,才能谋取比一辈子耕田更好的出路。如今,那些童年的甘苦已留在70后、80后的记忆里,我在《小镇往事》中就回忆过爬了25里的山路后,跟着小舅舅去仁居南门桥边那家望江饭店吃粄皮的事情。
读初二时,到村里过年的我开始给继祖母写春联、安装电线和电灯。或许,对继祖母来说,除了有伯父和父亲的关心,有我在的那些时光是她最为幸福的日子,埋在她内心最深的伤痕稍稍被抚平。继祖母的厨房打开门两头通,做饭、吃饭的时候常有人过来喝茶聊天,当中伴着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和调侃喧闹,还有我家的往事与历史。傻乎乎的我从来没有多想多问,多年以后才发觉那真是大损失,多少可以口述的历史事件和真相就这样白白流失过去,成为我如今要去做的弥补。
我考上高中到平远县城读书后,与村里的联系减少。更为不幸的是这一年,年轻时赣州老城区一带有名的美女继祖母溘然离世。因为遇到期中考试,父亲担心耽误我的学习没通知我送她老人家最后一程,成为遗憾!!!
15年后,家族亲情的传承让我与书园联系在一起。2005年12月父亲不幸去世,我接过照顾叔叔的重担。命运多舛终生未娶的叔叔一个人生活在村里,成了我心里剪不断的牵挂。叔叔这辈子最疼的人是我,舔犊情深自当回报,这一时期的经历对我来说可谓刻骨铭心。每年回到乡下第一件事情就是到书园,看看叔叔是否吃饱穿暖、身上缺不缺钱,给少了怕不够给多了担心被人诓。已经成家的我,终于进入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那时的叔叔是我回书园的原生动力。
2006年到2018年,是我人生中12年的煎熬和考验。那些年,我最担心看到手机来电显示乡下的电话,叔叔生活中层出不穷的问题往往让我感到束手无策、疲于应对。进入老年后,叔叔性格变得越来越固执,本来就有自闭症状的他更加难以接近、沟通,长年累月生活在被烟熏得漆黑的房里,吃喝拉撒全在里面,很多人都进不敢进去。那些年真的要感谢我那70多岁的姑姑和乡下的姐姐,姑姑每个月都要搭乘摩托车从另一个村一路颠簸过来送米送菜。被村里昵称为“摸耳姑姑”的她照顾完老母亲又照顾起她的哥哥。那时我们姑侄俩一通电话就是个把小时,老人家常常一边讲一遍掉泪,对叔叔是又气又可怜。如今,往事已经云淡风轻飘散于天地,它让我珍惜这份家族的血脉亲情,让我相信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挚爱传承,让我领悟到来人世间一趟亲人之间需守望扶持才能走好。
2012年春节前夕,我首次去寻乌项山帮叔叔办理养老补助,要在项山的信用社换存折和银行卡。那时交通没有如今便利,我得从书园返回平远辗转到寻乌县城、再到项山乡。时间紧迫,我像陀螺一样连轴转到没有停歇,因对政策和情况不了解结果连续跑了两趟。我回到书园安排好事情,站在祠堂前的门坪环看四周悲从心起,感叹如果爷爷看到叔叔这个凄凉模样,在天之灵一定会不安。
这一年,我过了一个心情非常沉重的春节,也经历了人生的中一次死里逃生。大年初二的晚上,身心俱疲的我在不经意中煤气中毒,被家人送到镇上的卫生院抢救。医生说如果再晚来十分钟,那就回天无术、神仙都救不了啦。这一次的“春劫”给了我巨大的震撼,我深深感受到人的生命原来如此的脆弱,要知道我是常年坚持羽毛球这项高强度运动的人呐。
劫后余生,我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感谢命运的安排,我决定给爷爷奶奶做点事,回报所有给我关爱的亲人。我再次充满情绪价值,坦然面对在照顾叔叔晚年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最重要的是,我于2013年开启了追寻爷爷历史的征程,执着与坚韧所取得的收获感动了无数人,以至于有一位上海的教授网友说我的努力是孝感动天。我还给了自己设定了学游泳的目标和挑战,并在2013年7月参加了广州市一年一度的横渡珠江,了却多年的一桩心愿。那些年,重生后的我如开挂了一般,很多朋友说我是因祸得福。
时间来到2018年,年迈体弱的姑姑也跑不动了。亲人们经过商量后,在村里的协助下,我将叔叔送到项山敬老院。送叔叔到敬老院的那天,我站在自家老屋遗址前怔怔出神,江西前些年出台政策要推掉空心房,那些经过历史和岁月洗礼只有残垣断瓦的房子就此消失。我不知道哪一间房爷爷和奶奶住过、哪一间房是父母的,自己在哪一间出生。当时有一个念头,今后可能没什么机会回来了,已无什么牵挂。口罩三年,我庆幸当初妥当安排好了叔叔,不然连进村里探望一下都艰难,跨省得做核酸检测和隔离。2023年的大年初六,叔叔走完他坎坷的80年人生路,刚上班第一天的我连夜赶回寻乌给他料理好后事,以不愧对叔侄一场。夜深人静之际,回顾叔叔的一生我写了美篇《若有来生,愿您再无忧伤孤寂》作为深切怀念,让不少人潸然泪下。
如今出走半生再品书园故事,意味悠长。这些年,因为寻亲缘故让我对书园又多了一份感情。除了我的爷爷之外,我家还有两位优秀女性——我的奶奶与继祖母(在早期的文章里为了区别,我称继祖母为“小奶奶”)都在这里生活、长眠。我的奶奶余文玉,还是一位彪炳史册的中国近代优秀知识女性。村里的奕书老师讲了一件往事,当年奶奶代爷爷给村里一位老人的大堂写了幅贺寿对联,后来时间久了对联脱落,但奶奶手写的墨迹依然留在墙上,可谓力透纸背。根据历史信息显示,奶奶不单止秀外慧中,还多才多艺。
奶奶来自山城重庆,重庆的“山”比起书园的“山”,那还是有明显差别的,毕竟重庆是城市,只是地势如山不平而已。书园的“山”是崎岖曲折、小路弯弯,听说当年爷爷携奶奶和伯父第一次回到书园,奶奶看到这种环境大为吃惊,她没想到爷爷的乡下是如此的偏僻和封闭,抱着伯父总想早点离开。但随着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怀孕的奶奶又从赣州回到了书园养胎。乡下传闻爷爷奶奶用英文写信的故事,应该就发生在这段时间,当时爷爷写给奶奶的信总被人偷看,他们夫妻俩一合计就想出了这个办法,被传为佳话。
1941年春,奶奶在书园因难产不幸去世,10岁的伯父和2岁多的父亲痛失至亲。如果不是伯父在赣州给奶奶制作了一块瓷像留存于世,父亲连奶奶长什么样子都记不得了。奶奶的去世对爷爷打击很大,如果当时有好一点的医疗条件,那么奶奶也不至于失去救治机会。后来,爷爷在当时的平远县城仁居购置了一间房子,房子靠近南门桥边、两层骑楼砖木结构。但遗憾的是时代一颗尘埃,又让这间房子离开了我家的怀抱,几年前它被推倒地皮被拍卖。
我一直以为端庄美丽的奶奶是大家闺秀,是上世纪二十年代读过大学的知识女性。所以,当我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找到奶奶的历史档案时被震惊到了,因为档案显示奶奶还是名留青史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兵队员。奶奶的战友中,有号称“黄埔女兵四杰”之一、国人熟知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其她三位为胡兰畦、游曦、胡筠),女兵队的每一个人都是有文化、有形象,都是百里挑一的巾帼英雄。
2020年5月,有幸找到奶奶兄长的历史档案后,我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公众号发表了寻亲文章《80年沧桑,跨世纪追寻》,盼望找到奶奶重庆的娘家亲人。这几年来,我从奶奶战友的回忆录中苦苦追寻她的名字和足迹,非常幸运也有所收获。2024年是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纪念,重庆当地热爱文史、关注黄埔女兵的网友联系了我,我补充了奶奶的部分历史信息并发表于网络。2025年三八节前夕,重庆档案馆的一位老师联系我,他找我确认奶奶在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简称“重庆二女师”)读书时的信息,因为奶奶正是从这间优秀的学校考取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
弹指一挥间,这一追寻也将近10年;如今追寻终于有所突破,愿上天不辜负我多年的努力与付出。待到那一天,我可以无悔的向天告慰亲人在天之灵。
奶奶在书园生活的时间不长,但我的继祖母赖运珠却是在书园度过大半生岁月。继祖母的名字是她与爷爷结婚后,爷爷给她取的。爷爷说过,他一生两段婚姻两位夫人中一位有文化、一位没什么文化,共同点是都长得漂亮和优秀。继祖母到老,都讲着赣州口音的客家话,她和奶奶给我定义了什么叫美女,奶奶端庄秀丽而继祖母则长得惊艳。但最让我敬佩的是继祖母那种骨子里的坚强,黎川曾有传闻说继祖母是当地的“豆腐西施”,被做县长的爷爷看上娶回了家,这是无稽之谈。真实的情况是,在赣州这座历史名城长大的她,是被时代的风浪冲荡到了书园。
自1948年底从黎川回到寻乌后,继祖母后半生几乎没离开过书园。在历史的风暴中,她死死的护住年幼的儿女,饱经坎坷的把下一代拉扯大。在黎川与爷爷分别时,她没有想到两人会阴阳相隔;因为那个时候,爷爷一定是嘱托她:“回去照顾好孩子,等我回来”。后半句继祖母没有盼到,只好等了四十多年后在天堂相聚。继祖母跟我说过,爷爷非常疼爱子女,她讲起爷爷时一脸投入和沉浸的样子,让我相信那个年代患难中的爱情比如今物质和浮华的婚姻,不知要珍贵多少倍!
父亲生前曾经讲过,继祖母的坚强和傲骨让他一生敬佩,她所经历的艰难要是换作普通人早就扛不住了。所以,继祖母去世后,父亲将爷爷留在书园的遗物与她合葬在一起,纪念她为潘家坚守一生!自此每次回到乡下,我都要去拜祭两位奶奶,曾经是父亲带着我,后来是我自己一个人或带着亲人,拜祭的对象多了父亲、叔叔。
追昔抚今,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书园的故事也在继续。随着村里拥有两位体制内副厅级的潘家优秀子弟叶锋与金城,众人对书园的关注度进一步的提升,有的朋友会联想到我笔端下写书园的文章,感叹书园是一块风水宝地。我自己的感受是,几年来认识的寻乌子弟越来越多,岽背在领先河、岽前正不断追赶。岽前的潘姓子弟潘震、源舟、其胜、晓明、忠义等等在广东都有好的发展,书园的其他小兄弟们也表现不错,潘屋的乾辉、其圣、赖屋的名金、名荣等,正在各自的领域发力。
2025年春节,我应邀在大年初二去了书园名金家。进入村口时突然感到茫然,一来担心有不少人认出自己,不知道去哪一家逗留、哪一家不逗留为好;二来又担心没人认识自己,像个陌生人一样的问路。这些年,村里有不少变化,我有时也会怀念那些消失的东西。在我纪念仁居中学百年校庆的《百年仁中,历史的邂逅与寻觅》中,就有读者留言提到村里乌泥坑屋背的那管泉水和石臼,瞬间也勾起我的回忆。那曾经养活潘家一代代人的地方,每天都人来人往的取水、洗衣、洗刷。后来有人图方便接驳了胶管和竹筒引水到家,荒废了石臼再也没有人气。自来水的普及又让这个陪伴了世代族人的泉孔退出历史舞台,想来甚为可惜!
名金说,书园的整体地形从上顺势而下到水口是一个八卦图,小河将村子一分为二形成天然的八卦图,真的是个非常好的地方。我没有去研究过,但思来应有灵验之处,这或许是书园蕴含的玄机之一吧。伫立在时间的潮头,回望一百多年来历史的风风雨雨,这个只有几百人的小山村养育出不少优秀的人,它就像寻乌项山的一道靓丽的风景,诉说着岽背一代代人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