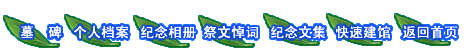可敬可爱的熊德輗老师
王立礼
2015年2月23日
熊老师忍受了多年疾病的折磨,他的走也许是解脱, 但是我听了这个消息还不免惆怅: 我所敬佩的英语界老前辈一个一个地离我们而去了。
我没有上过熊老师的课,但我的先生朱永涛在熊老师任课的实验班整整读了两年。1962年,李秉汉和熊德輗二位教授创立了实验班,他们二人力主精读泛读并举,整本书, 而不是一个个短篇, 进入主打英语课堂,让学生接触尽可能大量的英语exposure; 他们提倡read for knowledge,扩大知识面,阅读不同题材体裁的书籍和报刊文章。在李秉汉和熊德輗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朱永涛在两年学习中进步很快,虽然他提前一年被调出来当政治辅导员,学业上损失严重,但他的扎实英语功底使他日后在英国进修和在美国攻读美国史硕士学位都能胜任。说起自己的英语学习,永涛总是对二位恩师充满感激与敬佩。
1974年朱永涛去英国进修,熊老师给了他和英语系其他二位进修教师他的母亲蔡岱梅的住址,朱永涛他们拜访了旅居英国的蔡女士,受到她的热情接待,蔡女士还送给他们每人一本新出版的David Hawkes翻译的《红楼梦》第一卷 (英译名The Story of the Stone)。熊老师是个低调的人,大家都知道他从小生活在英国并毕业于牛津大学,但他从不以此自居,他没有宣扬过他的父亲熊式一先生所著的英语剧《王宝钏》曾在伦敦纽约上演近千场,轰动欧美,熊老写的英文小说《天桥》使他被誉为与林语堂齐名的双语大作家;熊老师也没有说过他的母亲蔡岱梅女士也受到高等教育,在英国出版了英文书Flowering Exile。当然,熊老师更没有提到他自己二十岁出头时就翻译过老舍先生的小说《牛天赐传》。我想,熊老师的英语如此精湛,汉译英的造诣如此之高,乃至受到全国学习英语学子的敬仰,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努力的结果,大概也继承了父母的英文写作的优良基因吧。
我虽然没有机会坐在熊老师的课堂里聆听他的讲课,但我应该算是他课堂之外的众多学生之一。在我教学的最后数年里,我主要担任汉译英课程,自退休后在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做志愿者十年来,也一直搞汉译英的工作。我发现,不论是学生(包括翻译研究生班,高翻)还是翻译志愿者,许多人的译稿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中式英语和明显的翻译腔。为此,我借鉴熊老师的汉译英的经验,仔细阅读他的翻译短文,在课堂上用他的翻译作为范文。我的学生说,读了熊老师的译文,犹如茅塞顿开,方知道好译文不是靠长句、难句和大词、难词、偏词堆砌出来的。他们看到,熊老师的译文虽然大多讲述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小故事,非常中国化本土化,但经过熊老师的妙笔变成英文后,读起来就跟新概念的课文一样有纯正地道的英语味。熊老师在《英语学习》上写的专栏文章成了我必学的读物。熊老师不讲很深的翻译理论,但他重视实践,并在实践中教学生如何突破母语汉语的思维框框,不被汉语牵着鼻子走,而是用自然流畅的地道英语呈现作品的原意。熊老师给我的启发和影响是非常大的。以上都是我觉得熊老师可敬之处。
熊老师为人宽厚,坦荡真实,和蔼可亲,幽默风趣,是一个可爱的长辈。熊老师热爱生活,他喜欢艺术,他开创了英语系每年一次盛大的English Evening之风,对此吴千之老师有生动的描写。相信英语学院许多老师都有在英语晚会登台表演的美好记忆。这不仅丰富了师生的文娱生活,更重要的是通过英语演出严格训练语音语调,使我们英语学院长期以来有着英语发音好的优良传统。
我家和熊老师同住北外西院几十年,走过北楼,经常看到熊老师站在门前,挺着圆圆的啤酒肚,笑眯眯地和大家打招呼聊天,逗孩子玩,这已成为西院的一个温馨画面。熊老师酷爱音乐,记得很早他就有了一套高级音响系统和许多古典音乐的盒式磁带。有时熊老师邀请朱永涛和我到他家听音乐。走进他的书房,坐在他那张一坐下就快塌的旧沙发上,看熊老师挑选一盒磁带放进录放机里,立刻,小小的房间满满当当地响起了美妙绝伦的乐曲。熊老师坐在录音机前,微闭双眼,轻轻地摇晃着头,完全陶醉于音乐之中,一幅心满意足、心情愉悦的神态。
还有一件能让熊老师心情无比愉悦的事就是每天喝点小酒。他的这个爱好在英语系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家没人喝酒,如果得到一瓶好酒,我们定会进贡给熊老师。无论是汾酒、五粮液,还是Black Label, Red Label, 熊老师一概来者不拒。每次他接过酒瓶子,脸上总洋溢着孩子般的开心。后来,熊老师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了,大家都劝他戒酒。有一次,别人送了我们一瓶不错的酒,永涛和我琢磨着还要不要送给熊老师,于是我们去问了熊老师还喝酒吗?熊老师说,“当然了,那是我生活的一大乐趣。”我们把酒递给熊老师,嘱咐他少喝点,他满口答应,频频点头,说道:“Everything in moderation.”好可爱的熊老师!
后来,我家搬出了西院,我见到熊老师的机会少了,最后见到他是若干年前英语学院一次年度聚会上,熊老师由家里的阿姨搀扶着走进餐厅,熊老师步履艰难,但脸上还挂着他特有的微笑。再后来,想去看他,但听说已经住进郊区养老院。我不知道熊老师最后的日子是怎样度过的,疾病缠身的滋味一定很痛苦,但我一想到熊老师,就似乎看到他脸上慈祥的笑容,在我的心中,熊老师永远是那样地可敬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