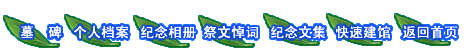三年同窗,一封信,五十年的歉疚……(散文)
李德文 2015/2/14 20:18:00 浏览:350
2014年9月21日,民勤一中高中64届毕业生在民勤聚会。这是50年来的第一次聚会,从各地来了20多人。除了告别这个世界的,和因病因事不能来的,能来的都来了。昔日的少年男女一个个都成了老翁老妪,聚首回顾往事,不免生出白云苍狗之慨。住在民勤城里的陈兆兰没能参加聚会,民勤的同学说是病了,因为怕聚会影响她的情绪便没有给她打招呼,并叮嘱如果我们之中谁去看她,也不要提及聚会的事。问什么病,说病在肺上,情况不太好。
24日聚会结束,我给她家打了个电话,她老公毛建中电话里说,他也正在找我,打了几次电话打不通,让我去他家里。10点钟左右到他家,陈兆兰病怏怏地从床上挣扎了起来,强打精神跟我说了几句话,老毛体贴地接过话头,述说了发病和检查治疗的情况—患的是肺癌,已经转移了。我听了心情很沉重,又怕她太累,安慰了几句便告辞出门。她坚持把我送到门口,我的眼泪已经忍不住了,不敢再看她,急忙掉头就走。
老毛把我送到大门口,我问他怎么没说找我什么事。老毛说,陈兆兰本来想请你给她写悼词,因为知道了你也有病,便没有让提。我说我是慢性病,一时半会儿还不要紧,老同学最后的要求,我一定要满足。于是约定次日上午再来听她讲述生平。
回到住处后心里很不好受,一直在想人生的无常,自然也想到了50年前写给她一封信。陈兆兰是我高中的同学,学习成绩在班上是名列前茅的,然而高考却落榜了。上中学时听说她家庭出身不好,至于怎么个不好法却不清楚。因为我家虽说是上中农,但因为父亲是所谓反革命社会基础,根子也“不正”;自己的情况尚且如此,又怎么好去打听别人的事情呢?
1964年秋冬之际,我收到她寄来的一封信,大意是说,她想明年改考文科,问我能不能把中学用过的文科复习材料寄给她。当时我们系正在搞小整风,批判学生中的白专道路,我是重点,正被整得焦头烂额。自己当时报考兰州大学中文系纯粹是出于爱好,想不到学文科跟政治有这么多的瓜葛,以至情绪受到了很大影响;再者那些复习材料也不在手边,忘记了到底还在不在。她的高考成绩我是毫不怀疑的,估计大学没能录取是因为家庭出身的影响,于是回信告诉她,改考文科恐怕也不一定能行,因为文科的“党性”更强……
从那以后,她再没有来过信,这成了我和她仅有的一次通信。后来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她的消息,说没有再考大学,也没有参加工作,后来又听说结婚了……而再次见面,却是在十三年之后。1977年10月中旬,武威地区文化馆馆长梁新民,委托我去民勤红沙梁公社孙指挥大队,找一个叫张有鹏的业余作者,谈他投寄给《红柳》杂志的一篇稿子的修改意见。谈完后闲聊,他说公社中学有个社请教师叫陈兆兰,问我认不认识。我说是同班同学,张便领着我去找她。
见面后她很惊讶,便邀我到家里去叙谈。那天是10月15日下午,好像是星期六,到家不久她的丈夫毛建中就从城里回来了。老毛很健谈,和我海阔天空谈了许久,吃过晚饭才告辞分手。那天晚上感慨万千,写了一首诗:隔绝音容十三年,乍逢尚觉如梦幻。少年壮志今何在,对坐相忆叹喟然。
20世纪80年代后,我每次到民勤出差有空就要到她家去一趟,一是看看她,二是和老毛聊天。老毛关心时政,和我很聊得来,也喜欢我去聊。我到金昌后,去民勤的机会少了。想不到这一次见面却要给她写悼词,心中的伤感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天我如约前往。她侧卧在病榻上,有气无力地讲述着,而我的思绪中却总是浮现着中学时的情景:1961年秋天第一次见到她,中等个,长得端庄秀丽,穿着也很朴素。她对学习抓得特别紧,一天到晚都在埋头读书,那种认真刻苦的劲头真是令人钦佩。我们在一起排演活剧《年青的一代》时,只要有空她就把作业拿出来做。她很能吃苦,记得有一次我向她请教一道数学题,发现她手心里长满了老茧。我惊讶地问她怎么了,她淡淡地说,暑假里给生产队提斡杆浇地磨的。
她是民勤县红柳园乡小西村人,生于1944年农历9月26日。父亲生了六个孩子,两个男孩,四个女孩,她排行老四。20世纪50年代土改被定为地主成分后,家境开始败落。因家中人口多,劳力少,缺吃少穿;后来父亲因修剪农业社果树,被人诬告砍伐树木,被加以破坏生产的罪名被捕入狱,1957年病逝狱中。从此以后,全家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她母亲虽是农村妇女,但对子女上学读书非常重视,长年用纺线织布、采摘枸杞换来的钱,为子女缴纳学费。上高小时,一次植树回家吃中午饭,母亲出外要粮食没有回来,她没有吃上中午饭,只好饿着肚子再去栽树。考上初中后,家中实在没有力量再供她上学,幸亏一位老师再三动员,才到民勤二中上学。当时,大姐、二姐正在上武威师范,从微薄的学费中省吃俭用,替她缴纳学费。上高中时大姐、二姐已经工作,便拿出一部分工资帮助她读书。
1964年高考时,她报考的是兰州大学化学系。兰大化学系是全国的名牌系,分配去向大多是科研单位。在当时阶级斗争讲得震天响政治氛围中,虽然她的数理化课学得出类拔萃,且不论地主家庭成分,仅就父亲病逝狱中这一条,政治审查肯定对她很不利。那时的她,怀揣着多么美丽的梦想,而又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啊!
当年秋天,苏山小学打算聘任她担任代课教师,被当时红柳园公社的领导以家庭出身不好为由拒绝。就在那时候,我的那封信又无情地击碎了她渺茫的希望。尽管拿惯了笔杆子的手提不动锄把子,尽管她不甘心,但走投无路的她,最现实的选择莫过于结婚了。1966年5月,经由别人介绍,她同毛建中结了婚。
老毛是红沙梁乡孙指挥村人,家庭成分也是地主,1963年毕业于昆明理工大学觅矿专业,在广东有色金属管理局工作。老毛理解她,并体贴她。二人生了三个孩子:长女毛霞、儿子毛晖和次女毛丽。老毛远在南国的广州,她苦苦厮守在塞北的老家,二人聚少离多,日夜担忧孩子的生活问题。长女毛霞出生时,因为老家分的口粮不够吃,只得赴新疆投奔公公和小叔,她没有奶水,靠那里的羊奶喂养大。毛晖和毛丽出生后,也遭遇了同样的困难,靠小米面糊糊加一点老毛从广东寄来的炼乳喂养。1973年元月,老毛从广东调回民勤,在政治歧视、经济拮据的双重压力下,二人以沫相濡,含辛茹苦地抚养着三个孩子。1976年,经过老毛的不懈努力,她当上了红沙梁公社中学的社请教师。
她虽然身体柔弱,性格温婉,却不愿向不公正的命运低头,曾多次奋力地拼搏、抗争。1978年恢复高考后,她报考了张掖师专数学系,那时她已经35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同时参加了县上招收高中教师的考试,先后都被录取。权衡再三她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于1978年底成为公办教师。1988年秋天,她投考武威教师进修学院培训班时,已经45岁,而给她上数学课的,正是中学的同班同学朱力学。后来几经辗转,她回到母校民勤一中任教,2000年底56岁时以中教一级职称退休。
三年同窗,一封信,50年的歉疚。后来我和陈兆兰见面都没有提起过那封信,也许是她忘记了?她不提,我也不好提,再说提起来又能说些什么呢?但那封信似乎是扎在我心头的一根刺,一旦被碰触就会隐然作痛,就像这次,还有1977年见面的那次。我追悔的是,当年那封信写得太草率了,说不定也是造成她坎坷人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假如当时我伸出援手,鼓励她改考文科,结果又会是什么样呢?会从细密的政治网眼中漏过吗?但时过境迁,追悔、歉疚,过去没有用,现在更没有用了——陈兆兰已于2014年12月14日凌晨三时告别了这个世界,她一生的坎坷和痛苦都归入了沉寂。希望她在通往天国的路上走好,假如有来生的话,更希望她下辈子投生到一个没有人为地把社会撕裂成两半的世界里,没有歧视,没有磨难,快乐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