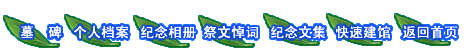申先生走了。
我认识申先生的时候,其实先生已经老了,我初认识先生,先生也已经是近七十的高龄。那时我眼中的他,与其他的老人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同。
先生是个热爱美食的人,家里一整面墙的玻璃柜子里,放了许多先生的“玩具”,都是些稀奇古怪的厨具。先生先是在上海江浙一代,后来去西南联大读书,再后来又留在天津,却是最早接触西餐的一些人。所以我从小跟在先生身边,倒是尝试了不少种类的西餐,尤其先生手制的苹果派,我十数年后仍念念不忘。现在想来,我后来如此热爱美食,也许与小时候在先生身边潜移默化是分不开的。后来先生做不动苹果派了,终于那些玩具都给了我,于是算是这些记忆也移交给了我。
可先生其实是个不服老的人。八十岁的先生手上没有驾照,可是看见我们开车回去,还是兴致勃勃地上去开了几十米。临近九十高龄,先生还念念不忘学问,成天坐在书房里堆得高高的书的中间,做学问写书。九十岁了,还辗转去参加旅游学术研讨会,去参加西南联大的纪念会。甚至直到今年早些时候,先生还有着满脑子的想法,可以与人滔滔不绝地说起旅游界的走向趋势。
先生子女孙辈常年在国外,与我们一家倒是格外亲近。我小时候一半的时间是在先生家里长起来,先生与夫人也一直对我视如己出。先生门厅里的冰箱门侧面,曾经常年的用磁铁贴着我小时候写的一篇作文,许多年了,甚至纸张都已经脆黄了,也一直没有拿下来。夫人早些年已经走了,现在先生却也去了,我倒有些怕再去看那间屋子。
先生家里客厅与书房其实是在一起的,先生常坐的那个书桌四周,都是翻得书页已经泛黄的书籍本册。桌上也从来都放满了各式的资料,却也有序。我儿时喜欢在先生桌上翻动,也会找到许多各式的照片,先生看着照片就能讲出许多故事。先生总说多读书总是好的,可说来惭愧,先生送的那套鲁迅全集我却一直没能好好地翻阅。可我从先生的身上学会聆听和讲述故事,这对我一生触动极大。
申先生其实实在是个有些传奇的人物。是在西南联大入学,可学还没上,便去了中缅远征军当了一名汽车兵。后来抗战胜利,又回到西南联大念书,最后在北京大学毕业。1980年,申先生去了南开执教,与那时一批学者一同创办全国第一个旅游系,从此在南开安居,转眼就是三十多年。
先生是个极有风骨的老人,骨子里透着的学者风度,是现时许多年轻人学不来的,厚重,体面,谦和,亲切;做起事来,又格外地执着而专注。我时常想念先生,这是个让人极为敬重的老人,而先生对我,其实更像是亲人。如今先生走了,我只是懊悔没能更多的回去看看先生。
申先生走了,享年91岁,留下我们这些后辈只能仍然想念着他。还好先生走的还算安详,先生忙碌了一辈子,这算是终于可以歇一歇了。
乍闻申先生仙逝,胡言乱语,仅为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