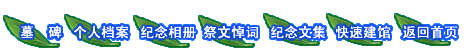母爱是我儿时小吃袋内的零食。酸辣咸甜,唯缺“苦”。这零食既解馋缓饥,也养体生津。成为我成长的第二奶水。它流入我五脏六腑,壮筋﹑补钙﹑润脑﹑益心。直到我年近古稀仍保留着这份眷恋——母爱的味道真好!
1959年——1963年,是我家国历史上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我读书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们少吃无穿,上学读书那是非常奢侈的事。母亲节衣缩食,从额外劳辛处获取,在日常牙缝里挤兑,硬是为我继续充实打造那个小吃袋。或上学时让我带着,或托人给我捎去。小吃袋内的零食还很丰富:或是母亲腌制的老酸菜(捞捞饭叶﹑马恋叶﹑羊掏叶,这些山野植物的叶子,内含有白浓的汁液,象母乳的奶汁。);或是母亲按压的辣芥菜;或是母亲炒制的土豆丝辣椒。还有桃干﹑杏干﹑葡萄干,炒面﹑炒豆﹑爆米花……每当我享受这些美味时,那酸辣的爽,咸甜的美由舌尖味蕾滋润我成长的心田。几种山野菜,几样土小吃,几十年后,竟成为现代人追逐的新宠。在那个困苦的年代,居然能享受到这些小吃,我从骨子里感恩我的母亲!
那是我七岁的生日,母亲蒸了几笼屉包子,全家人吃后,还剩半笼屉包子,母亲把它扣在笼屉内。到第二天再吃时,包子只留下空壳的面皮,馅儿都被我偷挖吃了。母亲心知肚明,欲笑还颦﹑抑庄扬谐指着空肚的包子笑说:“小老鼠偷挖了咱家的包子馅儿,咱就将就着吃点面皮吧!”我当时真想钻进地缝里。(在此之前,我曾被小老鼠咬过脚趾,对小老鼠非常厌恶)每当回忆起这件令我窘迫尴尬的事,包子馅儿的香甜并未给口齿味蕾留下多少记忆,倒是自责的酸楚和母爱的宽容时时撞击我记忆的闸门。母亲没有文化,也不懂教育,但她凭母爱的天性将“吹面不寒杨柳风” ﹑“二月春风似剪刀”的诗蕴吹进我自新成长的历程。这温柔﹑包容﹑批评的味道在我记忆的深处咀嚼:我象条嬉戏的鱼儿,母爱则是一汪碧绿的糊水,在包容我顽皮任性的同时,也将我快乐的漣漪一圈圈地扩散开去……几十年过去了,好奇﹑求新﹑追潮的个性在我心灵深处仍然激荡着。退休前,我怀着对课改的挚热情怀,撰文演讲,象蟋蟀唱出它一生最动听的歌;年近古稀,童心不眠,挟古稀观念涅槃,率童趣天堂虚拟,为父母献上一曲“云中之歌”。这桑榆夕阳的童趣,正源于伟大的母爱!
母爱散发着阳光的味道,阳光使人温暖,温暖莫过于母亲的怀抱。年幼时,我因淘气烫伤了右脚,哭闹不已,在母亲怀抱里扎腾的情形还依稀记得。当我有了儿子,儿子因疝气发作,连续两昼夜,儿子在他奶奶的怀抱里呻吟。我母亲一个姿势,一动不动地支撑着,手麻﹑臂困﹑腰酸﹑股疼,忍饥挨饿,硬是顶着直到孙子疝气消退。一个温暖的怀抱,该给子孙多少爱抚与慰藉啊!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夜幕降临,按说该是日息而休的时候,但母亲在打理完家务瑣事之后,又开始挑灯夜战。炕上扣个盆,盆上点盏灯,灯下忙营生。不是纳鞋补袜,就是缝衣做裤……我一觉醒来,只见炕头上摆放着做好的鞋袜衣裤之类,母亲又推碾上磨为家人打闹一天的吃食去了。而这也决非是日出而作的时候。那时,还没有粮食加工的机器,每天的饭食都靠人工碾磨而来。一个小村子没有几盘碾磨,要想占到碾磨,不早起是不行的。到吃早饭时,母亲已把一天的米面打理好了。还没吃过早饭,生产队上工的钟声就敲响了。母亲一天两出勤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劳动间隙,拾柴挽菜,养鸡喂猪,一直忙到夜幕再降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循环往复,母亲付出的是无尽的辛劳,得到的是无尽的苦涩。不管命运如何苦涩,母亲总是掏心吐哺,热爱儿孙。母爱伴随着儿孙一饮一啜,丝丝缕缕,绵绵不绝,于是在儿孙的笑声泪影中融入了母爱的无尽缠绵。我悟到了我儿时小吃袋内所缺的“苦”,全被母亲揽着。母亲吃苦耐劳的那份艰韧与倔强应该撑起后辈子孙生命的脊梁!
母爱的味道让我永世咀嚼品味!
(写于2014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