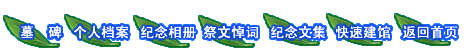那些年那些事那些话
一、父亲
父亲是2002年1月26日走的,享年79,虚岁80。那一年,我49,虚岁正好50。算起来,好像与父亲的相处时间有近半个世纪,其实不然。父亲自1959年被下放至富春江,到1983年底回杭,在这25年中,父亲应该每年有一次探亲假,不知那时是几天,至于其它节假日是否回来已经没有印象了。我仔细回想,6岁以前,除了幼儿园里有一个坟地边散步的恐怖场景,就没有其他包括父亲在内的记忆了。这25年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不会超过两年。父亲的好日子,是从1984年开始的,政治上平反了,又退休回杭,每天可以看书喝茶与老同学聊天,又因为退休关系挂在省电力局,所以参加了几次组织的旅游,只是那时还没有出国游,这对于一向具有家国天下情怀的父亲来说,也是他人生诸多遗憾中的一个。1990年1月8日,父亲患病手术,此后,除了医院,他不再下楼。
想到父亲,总是想起二个词,才华与悲剧,总是习惯将父亲的一生与时代与社会联系在一起,总是要感慨个人与时势与国家的关系,甚至和原生家庭的关系。父亲人生的辉煌时间,是在解放前学生运动到解放初期的那段时光。多年后,父亲谈起那些岁月,对往事依旧神采奕奕,对细节依旧历历在目,我记得的有,他一个晚上写了一万多的的文字,是浙江日报评论员文章;他抱着我,新华社的记者为我们拍了照;我记得最牢的是这样三句话,第一,多种花;第二,好事要赶快办,坏事可以拖一下;第三,要知道什么话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对什么人说。
这三句话,我不仅印象深刻,还身体力行了前面二句,愿意助人,不爱得罪人,工作中特别在后面十几年的办公室工作中,凡是领导交办的,政策上对大家有好处的事,巴巴结结地在第一时间抓紧办了,感觉对大家不是很友好的事,能拖则拖,拖不过去再说;而最最重要的第三句话,记的是当年父亲作为市委秘书科长,为了一个发言还是一篇文章,领导顾春林伯伯对父亲说了上面的话,父亲说他一直铭记。虽然我没有做到,但却是记的牢牢的。也曾把这几句话告诉过儿子,只是不知他记住没有。
二、母亲
母亲离世是2015年10月7日,因为过了生日,应该算是89岁走的吧?那一年我就要63了。除去下乡的5年,其实是4年,中间因为肝炎在家休养了一年,其他时间,甚至包括结婚以后,都好像没有和母亲分开过。所以记忆绵长却又具象,点点滴滴却又栩栩如生。可是细细想来,只有那句“我就抓住二个,一个是工作一个是子女”成了母亲的金句,深深镌刻在我和妹妹以及乒乒文文的记忆中。那么,还有许多许多的话语都去了哪儿?
母亲对我们影响更多的是她的身教。她乐于助人,一些在外人看来可能是抖来绑去的事,即使力有不逮,母亲也千方百计竭尽全力。比如她曾经为遭受出轨和家庭冷暴力的女教师出面打官司,促其离婚助其再婚;曾经将我山东表哥的女儿、南京表姐的女儿分别接到杭州,管吃住管学习,只是想提高她们的成绩;曾将我姨妈患病的女儿接到杭州住院治疗;主动为裁缝师傅的儿子寻找外语补习老师;为办公室同事寻找开刀医生东奔西跑。这样的事举不胜举,桩桩件件在眼前。
母亲另一个很突出的就是对待工人师傅的态度。小时候,房子坏了,水电出问题了,翻被子了,做衣服了,等等,在和这些劳工师傅们打交道时,母亲的热情周全至今记忆犹新,从称谓到茶水香烟,客客气气,从无责怪从无呵斥,支付工钱时,母亲总是说手头松一点,给的宽一点。凭着这份对师傅们的尊重,母亲也得到了师傅们的好感和关照,他们愿意留下联系电话,让母亲下次有事再去找他们。母亲的老家在安徽雄村,真正的大户人家,外公曾是合肥县长,反清革命党人。外婆是外公的二房,母亲仿佛始终记着在旧式大家庭中那一份寄人篱下的感受,记着10岁就开始的逃难求学生活中的种种艰难,以及解放后政治中残酷的一面,生活中冷酷的一面,她始终腰杆毕直,对上面对周边一些冷眼相看的目光不卑不亢,我行我素,而对那些师傅们,却礼数周全,尊敬有加。我想,一方面,母亲一人挑起家中所有大事小事琐事,上有婆婆,下有小女,她必得用心呵护,争取多方面的帮助。她曾多次说过类似的话,要结交三教九流的朋友。另一方面,则是母亲原生大家庭天生自带的教养和品质。我的理解是,这不仅是生活的需要,更是人情世故的底层颜色:相互尊重,相互帮助,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还有一句当下流行的注解:如何对待弱者,是一个人真正的教养。
已近清明,已是清明。在这行人皆断魂的时节,在这不思量自难忘的日子,写下如上,以示怀念。
燕妮
2020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