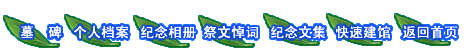父亲走了,在正月初四的傍晚。父亲生于1949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父亲走时,母亲和我们姊妹三个、两个儿媳、两个孙女和不满一周的孙子、外孙女和几乎所有的亲人都在床前。他老人家走得还算安详,肝癌、喉癌引起的痛苦时间并不长。虽然我们想方设法的治疗,从市医院到省二院、省四院 、北京同仁医院 、肿瘤医院都治疗过,做过超声刀、射频等手术。但还是没把他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父亲走时,什么话也没留下来。他的病我们一直瞒着他,开始他没意识到他会走,等意识到时已经说不出什么了。在他弥留时,迷迷糊糊说的全是村里的事,什么街里垃圾该清理了,变压器该修了等等。他当了二十年的村干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履行职责。虽然我们已经伺候了四个月了,但当他真的离去时,我们还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心都碎了。
父亲很勤劳。他出身贫寒,在姊妹六个中他是老大,高小毕业后,他才十五、六岁,就早早帮爷爷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先参加宣传队,后来当村电工,别的电工都是不忙时在供销社歇着聊天,而他在空闲时总是背着筐到地里割草沤粪挣工分。到改革开放后,他开始经商,先是和别人合伙开面坊,后来开油坊。家境开始慢慢好起来。尤其是在办起棉油加工厂后,渐渐成为最早富起的农民。就那样他还是那样勤劳,甚么活都时和工人们一起干,而且是带头干。从不在一边歇着指挥。在家里也是一样,别管晚上睡得多晚,早晨总是早早起来,扫院子、扫门前街道。后来乡里做工作让他当村支书,当时他的棉油加工厂正红火,而我们村里乱的不行,村经济一穷二白,没人愿意当干部。乡干部想让我父亲这个能人改变村里的面貌,就一直在动员他。父亲这个人很豪爽,架不住乡领导轮番上阵做工作。先是当村主任主持工作,后来入了党担任了支书。他一上台就不负众望。开始招商引资。先是找了石家庄一家军队办事处,在我村开石膏矿,我村以土地入股。后来又开办村石膏加工厂。村里富裕后,他开始为村里办实事。先上变压器、打机井解决村里的灌溉问题。又将村里所有的街道都进行了硬化。又立集市搞活商品流通。让一般群众能够做个小做买卖挣个钱贴补家用。后来又在我村搞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鼓励群众利用石膏资源优势办厂,经过几年努力。使我村摆脱了贫困落后的面貌,成为县里比较富裕的村。
父亲很节俭。他不讲吃不讲穿,没别的爱好,就是平常爱喝两口。他从来不买衣服,我母亲给他买什么,就穿什么。儿女们大了,在他生日时,给他买几件衣服,他平时也不穿。以至于在他去世后,我母亲从柜子里拿出好几件衣服,流着泪说这些衣服你爹都还没沾过身。他抽烟从来不抽好烟,说好烟没劲。喝酒也不讲究,什么酒也能喝。五块钱一瓶的老村长他照样喝得津津有味 。更不讲究菜,剥个生花生仁下酒,是经常的事。过年过节,儿女们给他拿的好酒好烟,他自己总舍不得喝,等家里来了客人,却也很大方的拿出来让大伙放开喝。一边喝一边说:烟是小子给买的,酒是闺女给拿的等等。他是在显摆自己的儿女有本事,为自己能有这样有本事的儿女自豪啊!在住院期间,他总是念叨,已经花了好几万了。我的病没事,别再花钱了,我回去把烟酒戒了,再吃点药就好了。父亲啊,你辛苦了一辈子,给儿女吃了这么多的家业,怎么连给自己看病花钱还舍不得啊!
父亲很豪爽。走路步子很大,干起活来动作很大,也很快,乡下话叫出活。而且总嫌别人干活慢,家里的活从不让儿女们插手,用他的话说嫌我们不中用。就是在农忙时,也不让我们回去。说你们回来我还得伺候你们。说话嗓门很高,我母亲总说他说话总想和别人吵架。脾气很暴躁,年轻时,几句话不和,就能和别人动拳头。他的豪爽仗义在附近三里五乡是出了名的。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很敬佩他。在我们乡里工作过的人,调走后有事会到乡里,总忘不了给他到个电话,一块喝几杯。平时家里总是人不断,乡亲们没事总愿意和他聊会儿天,喝点酒。每逢这时,他也总是毫不吝啬的把家里的好烟好酒往外拿。谁有事求他帮忙的,他总是热心的帮忙。有时自己赔着钱跑。他总是教育我们,乡亲们用着时,一定要热心,能办时办,不能办事也要热心跑。他下葬那天,乡亲们都说,这么多年了,下葬这么多乡亲主动去坟上的,在我村很少。给他的评价是:说话难听,但是对人没赖心。
父亲,祝你在天堂过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