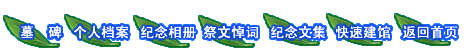今天,我参加纪念我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作为家属,内心非常激动。首先,我父亲逝世将近二十年了,今天举行这样隆重的纪念仪式,使我感到,在我们国家里,一个人只要对人民作过一点有益的事,不管多少年后,国家与人民不会忘记他,仍然垂念其贡献。
我也要感谢今天到会的,曾和我父亲共事的老前辈,现在大多已经高龄了,但是仍然珍视和我父亲的友谊,坚持新版来参加纪念仪式。
作为家属中,也要感谢药物所筹备这次纪念活动的各位同老,他们化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到了北京等不少地方,搜集资料,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举个例子来说,我父亲生日是农历十一月初五,当时还是清朝,不通告今天的公历,知道举行这次纪念仪式后,我查了一下日历,今年的十一月初五是公历12月16日,所以,我一直认为纪念仪式将在12月16日举行,但是药物所的李静珍等同志,特地到天文台去查了,100年前的十一月初五是12月11日,所以,纪念仪式才订在今天,由此可见,他们对这次纪念活动的筹备是如何郑重而周到了。
我原想借今天的机会,介绍一些我父亲的家庭生活情况,但是,想来想去,谈不出什么。因为,一来我父亲的生活非常简单而刻板,而且还十年如一日,没有什么变化,而且,说来使人不信,我和他一同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接触的时间并不多,他每天的生活是,早上起来后,先打扫一下房间,特别年龄大了以后,他认为一定要每天坚持作一些体力活动,然后上班,中午12点钟回家,从不早,从不迟。午饭是便宜人惟一在一起的时间。在餐桌上,他从不提起他的工作,他尊重自己的业务,决不在餐桌上随便谈论,也从不愿意谈论他自己。1966年,他死前几个月,我姊姊回国来看他,我告诉我姊:70岁生日时,药物所曾将他的工作情况,拍摄过不少照片,在午餐桌上,我姊姊提出要看这些照片,我父亲没有回答,还有些发怒。平日午餐后,我父亲午睡一下,准2点上班,准5点下班,回到家里,就回到自己房间休息,晚餐是单独吃的,也不愿意家人到他房间去打扰他。晚上10点,他睡觉。几十年如一日,天天如此,70岁前,是期日下午,他有时在家庭附近散步一下,不超过一小时。70岁以后,有段时间,药物所为他影评了一张文化俱乐部的出入证,他是期日下午就到文化俱乐部打一回弹子,吃一顿晚饭。我从未见他去听过一次戏,也未见他看过一次电影,家里也从无客人来吃过一顿饭。最近,我和丁光生伯伯一同去机场接外宾,途中,丁伯伯谈起,他1951年回国时,我父亲曾请他吃过一顿饭,我当时已记不起此事,后来仔细回忆,确有此事,那是为了药物所要建立药理室的缘故。因为,解放前,药物所药理室的工作,都是将样本送往美国请陈克恢先生做的,解放后,我父亲决心在所内自己建立一个药理室,所以请丁光生伯伯从美国回来,主持这工作,为了建立药理室,破例请他吃了顿饭,事实上,就是家里烧了三四个菜,但是,对他来说,已是千年难有的事了,此外,就是过年过节,也从无客人来吃饭。今天纪念他诞辰,对他来说,是第三次,此外,就是70岁和80岁两次,药物所为他庆祝了生日,他自己从不提到他的生日,我也不记得他生日是哪一天。
我父亲做事,都是事先考虑周到,然后再做。平日,他叫我作些什么事,都事先反复讲清,第一步如何做,第二步如何做。他自己做事也是一样,总是充满着自信心,从容不迫,有条有理。就以他死的那天来说,那是1966年夏天最炎热的一天,他在房内午睡,当时,我女儿还小,下午拿报纸到他房里,他昏睡在床上,我女儿喊他起来,他挣扎着起来,随即倒下,然后再挣扎坐起来,将衣服鞋袜,一一穿整齐,扶着写字台,走到他的圈椅,端坐下,随即倒到地上死了,我赶回家后,因为要知道他的死因,给他测了一下体温,体温表上,水银柱已经到顶了,但就在这样情况下,他还是坚强地,冷静地把衣服穿整齐,端正坐好,然后倒地死去。事实上,在他80岁后,他就几次说过,再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即使活着,人也没有力气,不能再工作了。
占据他整个心灵的,是他的研究工作,他的实验室。从药物所建立起,他就把它当做终身工作的场所。药物所是在9月份成立的,所以,建所工作是在大热天进行的,他每天上午都亲到现场主持工作,将所有的橱柜,里外都涂上漆,这就是他要把这个所成为他终身事业的决心。太平洋事变后,日本人看中了药物所的设备,当时药物所的设备,据说在远东是数一数二的。有一天,日本人突然来到所里,将设备全部搬到黄浦江边的船上,准备立刻运往日本去,我父亲立刻赶到法国驻沪领事馆,提出药物所建所的经费是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日本人无权如此做,当时即由法领事通知码头上的巡捕,将船只扣留,不准启航,并由法公董局教育处长Grobois亲自去码头,将仪器设备从船上搬回,事后,日本宪兵队几次传讯我父亲,我父亲始终冷静应付,并未逃避,为的是要保全这个所。上海解放前几个月,有一天晚上,李石曾先生到我们家来,告诉我父亲,船已经准备好,要我父亲将所搬到台湾去,我父亲说,这些设备是不能拆,不能搬动的,李石曾先生也没有坚持就走了。临解放前几天,朱洗伯伯到我家来,和我父亲商量下一步工作,我正好端茶进去,听我父亲说“内战结束以后,国家安定,科学事业会有发展的机会,特别你年纪比我轻,还能好好做一番事业。”可惜,以后朱洗伯伯因为患肺癌,比我父亲先死,这是当时没有料到的。解放以后,也有几次谈到药物所要搬出武康路,但是,我父亲始终不搬,因为,这个实验室,这个所,是他决心终身工作的场所。一直到他临死一天,他上午还去实验室工作,但是,这一天是唯一的例外,他早上10点钟就回来了,说“今天实在不能支持了。”当天下午,他就死了。
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我记不起他身前讲过什么豪言壮语,也记不起他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像一个苦行僧,在晨钟暮鼓的伴随下度过其一生,我的父亲,他坚定的将他一生献给了药物研究。他考虑一切事情,都从一点出发,就是如何能不受干扰,坚持他的研究。他放弃了个人的乐趣,他人生的惟一目的,就是埋头于发现新的药物品种,他将一生在实验室里,在药物所渡过了。在我的记忆力,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赵体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