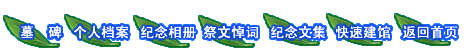外婆离开我们已经有12个年头了,从我18岁离开家乡,独自到异地求学,外婆与我生活的交集打有记忆算起,也不过十多年的时间。这样一个坚强苦难的女人,一生拉扯着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后来又带着四个孙子孙女、四个外孙外孙女长大,把一生全部的光阴都奉献给了这个家族,没有任何抱怨,最后在疾病的折磨中,艰难的完成了他人生的旅程。
记忆的碎片在时间的流逝中慢慢消散,头脑中外婆的样子也越来越模糊了。像夜晚薄雾之中站在你面前的影子,你越想看清她的面庞,却越是消散的仓促;但唯有那一双慈祥而深凹的眼睛,烫得像撕破黑夜的北极星,久久注视着你,让你不能忘怀!也正是这一双眼睛,在数不清的傍晚落日的余晖中,目送着我幼小的背影,守望着我的童年。
俗话说,外孙没有里孙亲,但是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外婆对我和妹妹却格外的亲近。我和妹妹也是一到周末就迫不及待地往外婆家跑,直到周日晚得不能再晚才回家,然后掰着小手指头数,还有几天才能再来外婆家玩。外婆做得一手好菜,总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将几个稀松平常的食材,做成人间美味佳肴,记忆中深刻至极的就是外婆做的喜坨鱼下面条了。奶白奶白的鱼汤,宽宽的面条上点缀着几颗飘着清香的小葱,那是我们馋涎欲滴的美味。后来这道手艺自然而然的传承到妈妈那里,每次吃起,都飘散着外婆面汤的味道!
现在的我还算沉稳,但孩童时代的我别提有多调皮了。走路从来不走正道,哪里有坡坡坎坎,哪里有荆棘丛生,哪里有毒蛇出没,就我就专门走哪里。所以你可以经常看到我衣服的袖口是稀边的,裤脚也是脱线的,最要命的是每一双鞋子穿不到两个月。别人家的孩子,鞋子要么是鞋底磨破,要么是鞋边脱线,而我的鞋子却不是这样,所有的鞋子都是脚尖和脚跟处破烂。这大约是我平时不走正路造成的,总是用脚踢杂草丛中的石头和长满尖刺的树枝。星期天外婆送我回家,我在前头的荆棘丛中穿行,外婆在后面紧紧跟随。她一边赶路,一边不停地唠叨:“就算给你穿上铁鞋子,你也会把鞋跟穿破!”可是那个年代没有铁鞋,有的话,外婆一定会给我买一双,因为他最不愿意看到我挨饿受冻。所以,时光可以倒回的话,你能够经常看到寒冬腊月的夜晚,我们都在温暖的被窝里熟睡了,而外婆却在烛光下给我们缝袜子、补鞋子,绣花针在她花白的发间刮过,然后在带着顶针的手指和鞋袜之间飞快地翻飞;你也可以看到,在午夜挂钟钟摆滴答滴答的流淌中,外婆把挑秧用的铁丝簸箕倒扣在烧得旺旺的煤炉上给我们烘烤白天里疯逗打闹弄湿的厚厚的棉衣棉裤。早上从被窝里钻出来的那一刻,最怕的就是从门缝里钻进来的那一缕缕遭受大雪拷打的寒风,总是迫不及待地穿上外婆递过来的烘烤了一个晚上的棉衣,那种温暖迅速包裹全身,舒服到骨头里。那时候还不明白,以为温暖的是炉火,却不知道是人心呐!多少年以后才发现,炉火还可以在,但那种温暖到骨头里的满足再也不在了。
到了2001年,我考进了军校,每年回来的时间更少,但每次回来,我都要迫不及待地去看我的老家家。那个时候每个月能领到100块钱的津贴,每次回来还能有点积蓄,给家家带点小东西。每次看完家家离开的时候,我总是想方设法的在家家房里的被子上、枕头里、抽屉中或是米缸里,偷偷藏上几百块钱,回到家了再打电话告诉她。那是因为有一次走的时候,把钱压在水瓶底下,被家家及时发现了,跑出来追了我一路,我又不能回头,又怕他摔倒,搞得十分狼狈。读了军校,家家对我念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是国家的人了!我是国家的人了?那个时候刚读军校,每天教导员不离口的话是“完成两个转变”,就是从一名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转变、从一名老百姓到革命军人的转变。俏皮的话总是没有平凡的话更能让人入心入脑。“我是国家的人了!”一句多么平凡却满怀自豪的话,是它让我顺利完成了两个转变,是她让我明白我的生命和价值都要奉献给国家。
再往后的事我不愿写也不愿想了,想起来太痛苦。瘦骨嶙峋、满背褥疮、最后拉的像蛛丝一样细长的气,还有那突兀的颧骨和深张的口......学医出身,看多了生老病死,原想不过落叶归根,新陈代谢,但家家走的那个晚上,瓢泼而下的除了帐篷外裹着哀乐的大雨,还有我痛彻心扉的眼泪。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无情地碾压荆棘丛生的记忆,那些陈旧的故事,终将会在寂静无声的黑夜,被凛冽的寒风撕成灰烬。但外婆的音容笑貌和只言片语,就像海上的灯塔一样,穿越时空的氤氲,永久地守望着我,守望着你。就像每一个周末天幕笼罩的夜晚,那条蜿蜒狭窄的乡间小路的尽头,参天的大树下,一位拄着拐杖的老者,目光柔和的守望着你,不愿离去,直到你消失在她模糊的视线里......